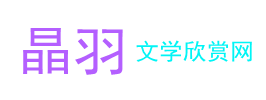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诗歌与音乐的关系的名言)
在“诗乐年华”中感受音乐之美,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1
作者:张璐(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陈盼,系青年指挥)
日前,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圆满落幕。合唱节以“诗乐年华”为主题,通过大师课、艺术讲堂、公益演出、展览等形式,让观众得以全方位参与到合唱中。
合唱这一艺术表演形式是舶来品,约19世纪由西方进入我国。直到20世纪初,这一艺术形式开始被人民群众所熟悉,并随着近代新学堂的建立而逐步扩大影响。作为一种多人合作的演唱形式,合唱必须由一个演唱集体来完成,也正是因为集体学习、演唱、表演的特性,使合唱的情感表达功能、教育功能及社会功能比其他音乐形式更为显著。
近年来,中国合唱团在世界合唱舞台上大放异彩,国内听众也因为在合唱表演中感受到更多耳熟能详的曲调、深有共鸣的文字,所以更加愿意走进音乐殿堂,聆听高品质的音乐会,感受音乐之美。
本届合唱节中,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激情演绎的经典作品《黄河大合唱》采用了诗朗诵与音乐并重的表演形式。这部由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六天六夜不眠不休完成的传世之作,曲与歌词、朗诵与演唱相得益彰。此次演出选择了由我国著名指挥家严良堃改编的双钢琴伴奏版。作为冼星海的学生,严良堃是这部传世之作的重要传播者和见证人,早在1940年就曾亲自指挥过《黄河大合唱》,观众最为熟悉、上演场次最多的中央乐团演出本(管弦乐队版)也是由严良堃牵头,组织几位著名作曲家共同编创的。
八十多年来,《黄河大合唱》在国内外的音乐舞台上不断创造辉煌,除了作品本身所拥有的波澜壮阔之力,同样也离不开几代文艺工作者的血脉传承。合唱用其极强的表现力精准表达了复杂而细腻的情感,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具有的多声部的音乐配合、多层次的力度表达,都是个体艺术难以达到的。
合唱节的开幕演出“古韵·诗律”中,著名指挥家吴灵芬带领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为观众献上了《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花非花》《观沧海》等优秀的古韵新作,并演绎了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清唱剧《长恨歌》。
古典诗词与当代音乐碰撞,完美融合了诗词精华与音乐气韵,赋予古韵新的生命力。合唱节期间还上演了作曲家罗麦朔的两首作品,其中《观沧海》选自其17号作品《步出夏门行》,歌词来自曹操同名组诗。《观沧海》全曲采用密集的三连音伴奏织体,从诗人眼中所见之景沧海澹澹、浩渺澎湃,描绘至其心中所想日月明耀、星汉灿烂,意味悠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曲家在以传统调式为基础建立的旋律线条中加入了短暂的离调,于“树木丛生,百草丰茂”处制造了一个突如其来、却顺应诗作原意的转折,上承“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下领“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突然紧张后又回归原素材中不断发展的和声音响,让曹操戎装在身、登高远眺、以诗抒怀的形象得到更为准确、立体的塑造。
在合唱团中,团员必须拥有极强的团队协作精神,他们需要尽最大可能地抹掉个体发音特质、减少个体差异,进行合作演唱。指挥家常说,“合”字由“人”“一”“口”组成,一人一口即是合,强调合唱中的统一性、整齐性以及声部合作之间的均衡感。
应当说,合唱始终在寻求一种动态的共性,一种需要齐心协力来完成的动态平衡,只有通力合作,对审美有着相同的价值认同,才有可能完成作品。作为观众,在欣赏合唱作品时,往往也需要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声歌唱也会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团队的力量与支持,获得无与伦比的幸福感。
本届合唱节上演的清唱剧《长恨歌》由黄自创作完成(黄自作曲、韦瀚章作词、林声翕补遗),这部作品作为20世纪为数不多的大型声乐作品之一,是作曲家黄自运用西欧创作技法进行音乐民族化的一次尝试。其中,在第八乐章女声合唱《山在虚无缥缈间》中,作者采用复调技法来描绘蓬莱仙岛朦胧缥缈之景。将合唱中女声三个声部剥离来看,他们各自拥有优美动听的旋律,而总体细品又可听出相互间的模进关系,高、中、低三个声部依次出现,后面出现的声部形成了对前面声部的模仿与发展。这样一来,三个声部互相支持、互为补充,每一次声部进入之时,其他已在旋律行进中的声部都需要有意识的避让,无论是从音量、音色,还是从音质、情感方面,都需要相互聆听与模仿,合力为听众描绘层层起伏之景。
合唱作为声乐表演艺术的一个分支,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它主要属于音乐范畴,但同时与文学、历史、社会等其他多学科紧密联系。合唱通过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在未来必将会得到我国观众更为广泛的喜爱与认可。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8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2
《经典咏流传》剧照
出品方供图
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渐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拓展了广阔天地和无限可能。在这场澎湃的“国潮”之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咏流传》等文化音乐节目表现亮眼,在推动经典诗词大众化、现代音乐经典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艺术教育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重温千年前的诗乐和鸣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一千多年前,李白客居洛阳,夜深人静之时,被一曲笛声唤起思乡之情,提笔写下这首《春夜洛城闻笛》。以诗应曲,以柳寄情,从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2022年4月,在《经典咏流传·大美中华》的舞台上,邓小岚女士与她创立的马兰花儿童合唱团共同唱响这首经典,并迅速登上热搜,引得无数网友“破防”。
好的音乐不仅打动耳朵,更直抵心灵。邓小岚18年坚守音乐课堂、点亮山村孩子梦想的精神,于我心有戚戚。作为文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我深知音乐对人的美育价值和塑造能力。舞台上,孩子们身上散发的自信和眼神中闪耀的光芒,既源于经典穿越时空的吸引力、创造力,也得益于音乐带给人的生命力、感染力。
这不是《经典咏流传》第一次“破圈”。从第一季至今,这个舞台上诞生了《苔》《少年中国说》《岳阳楼记》等一大批广为流传的曲目,第五季节目中的《忆江南》《节气歌》《风》等歌曲也受到好评。这些歌曲将历史纵深与厚重文化纳入胸怀,以音乐唤醒诗词,用歌声致敬经典,促进了古典诗词文化的全民传播,既咏唱经典,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的经典音乐作品。节目所取得的热烈反响,不仅源于守正创新、精益求精的创作理念,更体现出古典诗词与民族音乐内在的和谐统一。
古典诗词在诞生伊始,就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诗经》300余篇中,几乎均可和乐歌唱。这种“和诗以歌”的形式,从源头奠定了诗词所蕴含的韵律美、声调美、节奏美等基本特征,使得诗词与音乐成为天然的“搭档”。因此,与其说《经典咏流传》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毋宁说,它是在追寻并努力重现千百年前音乐与诗词如同高山流水一般的“相遇”。
千百年后,当言简意丰的古典诗词与千变万化的现代音乐再次相逢,不仅有效放大了诗词所承载的情感张力,更显著提升了音乐的文化价值和艺术美感:可以展现“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的自信豪迈,亦可表达“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淡然……或浅吟低唱,或引吭高歌,音乐一起,便将观众带入历史的长河,沉浸于诗人的情感世界,生出许多共情与和鸣。
诠释经典背后的民族精神
“和诗以歌”,不是简单地为诗词谱上曲,也不是将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进行生硬地嫁接,更无意从考据的角度为每一首诗复原对应的古曲。回溯节目不难发现,几乎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以背景解析为开端,以当代价值为落脚。经典传唱人着力探寻的,是诗词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从思乡愁绪到生命喟叹,从人民情怀到万里江山,经由音乐助力,其中的情感、价值观得以自然抒发,给人带来温暖和鼓舞,彰显出独特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本季《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来自祖国东南西北边境的4位移民管理警察唱响毛泽东同志经典诗词《菩萨蛮·大柏地》。4位国门警花飒爽的英姿、嘹亮的歌声、动情的讲述,深深震撼和感动着每一位观众。
我出生、成长在西部边疆,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沿着祖国的边防线和海防线,每年为基层战友送上100多场慰问演出。我常常想,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在极端苦寒的环境中坚守,又是什么引领着我坚持为他们歌唱?毛泽东同志的这首词提供了答案——“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是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满腔热爱激励着我们从“小我”走向“大我”,从大美河山中激发起万丈豪情。
这是经典的魅力,也是艺术的力量。它们引导着我们跃入历史和生命的纵深之中,感悟先哲智慧,探寻英雄足迹,传承民族精神,走向美好未来。
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这一季《经典咏流传》以“大美中华”为主题,以诗词之美、音乐之美,展现自然山河之美,领悟历史文化之美,感受中华精神之美。期待更多的文艺创作者和艺术教育工作者,加入这张“大美中华”画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勇立潮头、奔涌向前。
(作者:王宏伟,系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3
《唐诗三百年》,黄天骥著,东方出版社中心,2022。
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经典——刘勰的《文心雕龙》序志篇开篇即提出:“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探讨作家作品“为文之用心”的创作论,应当是文学研究和评论的重要任务,对于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更应如此,对作为诗的国度的代表——唐代诗歌,尤应如此。这就有了黄天骥先生的“冷暖室古典文学创作论”之《唐诗三百年:诗人及其诗歌创作》。这是黄天骥先生从教六十余年来诗歌创作与研究的结晶。黄先生幼承家学,后又从詹安泰、黄海章等前辈学习诗词,在教学研究生涯中,虽然以戏曲为主,但也长期讲授诗词,并出版过《黄天骥诗词曲十讲》《诗词创作发凡》以及《冷暖室别集》等。所以,陈平原教授在《南国学人的志趣和情怀》一文中说:“顾随的弟子叶嘉莹在南开大学以及全国各地讲授古诗词,受到热烈追捧。以我对黄老师的了解,若愿意暂时搁置戏曲研究的重任,专心经营诗词曲的讲授,其效果当不在叶嘉莹之下。”
当然我们不宜斤斤于二位先生讲授效果之高下,但可讨论其各自的特点,方最有裨于读者;再则,《唐诗三百年》,也实可当黄先生的唐诗讲稿看,他确实在细心地教我们如何阅读和理解唐代诗人及其作品,用一句简单的行话,就是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读唐诗。我们不妨从黄先生解诗的两个特点谈起。
首先是创作体验,诗心相接,碰撞激发。日前看到程千帆先生1998年10月12日的一段讲课录音,说他们当年去胡小石先生家上唐人七绝的课,胡先生给他们讲柳宗元的《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讲着讲着就拿起书唱起来,唱了五六遍,然后把书一摔:你们走吧,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了。程先生对此印象非常深刻,认为胡先生为什么讲得那么好,是因为他“拿自己的心,去爆发了火花,去接触唐朝诗人的心,心与心相碰,是一种精神上的交融”。黄天骥先生讲唐诗本质上也是这样,但形式上则大异于这种太过传统的方式,而充分照顾到了新时代的学生的特点。比如他给同学们讲《春江花月夜》时,便先创作发表了体式和风格相仿的《花市行》,虽然被黄海章教授批评不该效法初唐体,内心却是窃喜——效仿的成功,证明能得初唐诗人的诗心。这样,给同学们讲起来,才能古今一体,师生一体。所以,当年“新三届”的本科同学每次毕业聚会,必再请黄老师重讲此诗,以为最佳的纪念。后来黄先生给我们讲吴梅村的《圆圆行》时,则提供一篇匿名的《珠水吟》供大家当靶子攻击完后,再从歌行体发展的历史,综合分析历代名篇的优劣得失,也中肯指出《珠水吟》的可取与不足之处,并直言相告,此乃“拙作”。所以,探讨诗人之用心,既要知人,讲诗人一时之用心,也要论世,讲诗歌写作的情境,甚至其时代背景,还要讲诗歌及其体式发展的历史,这样才能把诗人创作之用心及诗篇杰出之所以然讲深讲透。像本书中收录的《说李白的》,从猿啼意象入手,历证其向为悲苦之声,但为什么在李白诗中来了个大逆转?这完全是李白异常心境的投射:他行到此处突然遇赦了——此前他是“世人皆欲杀”(杜甫语)之人,现在他遇赦了,是令人狂喜的事,但高傲的李白却不肯正面表露。如此,全诗纯以景语写之,表面轻快之下,实寓万钧心力,故能惊风雨、泣鬼神,力压三唐。
其次是以戏剧与音乐的眼光讨论唐诗的描写及其结体特征。无论戏曲与音乐,在黄先生都属本色与当行。黄先生是古典戏曲研究的名家,长期兼任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他的古典文学创作论系列研究与写作,也正是从戏曲开始的,目前已出版《情解西厢:创作论》,《意趣神色:创作论》,备受学界赞誉。黄先生常说他“带着诗词的眼光去研究戏曲,又带着戏曲的眼光去研究诗词”,于诗词与音乐的关系亦然;黄先生曾亲炙名师学习合唱指挥,迄今仍指挥学校诸多大型演出活动,每令专业指挥人士心折。我们先看这种指挥艺术对黄先生歌行体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善于经营长篇巨制。比如他创作的《围棋咏》,完全是岑参边塞诗的风味:从大将出征到凯旋,从运筹帷幄到短兵相接,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有四面楚歌直捣黄龙;每四句一转韵,每韵都有独立的事项,环环相扣,首尾呼应;诗中关于围棋的典故、术语也都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一曲读完,余音袅袅,诚如听完一曲交响。其实黄先生这首歌行体诗的这种乐章结构,也像戏曲的分场与戏剧分幕。借着音乐与戏曲的修为,他分析王昌龄的《出塞》(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便戏味盎然。特别说到诗的第四句“匣里金刀血未干”时:到底将军是顿时拔起鞘里带血的刀,还是立刻想起腰间那把还带着敌人血渍的刀?诗人都没有细写,但是,无论将军是拔出刀,半拔刀,或者未拔刀,总之,他的注意力,全在刀上。很明显,他是在准备战斗了!整首诗,就在写这将军突兀的神态中结束。这种“结束”,其实就是戏剧的“停顿”,也像乐曲在进行时出现“休止符”,片刻的旋律和节奏停顿,才又重新开始,反而会加强听众对乐曲的印象。这种“结束”,也像传统戏曲的“亮相”,指演员在一连串连续性的动作中,突然作短暂的中止,呈现出一个具有雕塑性的造型——战场上虽已寂静,但交战的状态,还未从将军的心中完全平息;他忽然似乎听到战鼓在响,似乎感到敌人又在临近,于是猛然想到,或者立刻拔起已经入鞘的带血金刀。整首诗,就在他将拔欲拔的细节中定格。通过这动作,将军警惕的神情,坚毅的态度,便如戏曲演员“亮相”一样凝聚在读者的脑海里,诚属“武戏文唱的妙用”。
于诗如此,于词亦然。黄先生曾在分析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全篇结构时说:“显然,经过一番衬托,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的主角。我觉得,苏轼在《念奴娇》中的表现手法,和上述元帅出场的模样颇为相似。请勿以为他突出写周郎,便以为他以周郎为主角,其实,最后出场的元帅,正是苏轼自己。多情的周郎,也只不过是配角。”对此,陈平原教授说:“《赤壁怀古》中‘周郎是宾,自己是主’,清人已有言在先;但引入戏曲表演的‘元帅出场’,此前我没见过如此生动的解说。这显然与黄老师兼及诗词与戏剧的治学方法有关。”又说:“很少学者同时研究‘唐诗宋词’与‘元明清戏曲’;即便这么做,成功的几率也不高。而对于坚信‘岭南文化’的特点一是包容、二是交融的黄天骥来说,诗词与戏曲互参,属于‘打通了,事半功倍’,故值得认真尝试。”
从创作体验入手,以戏说诗,以音乐说诗,诚可谓黄先生开辟的古典诗词讲授的另一种范式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本书最引人注目的成功之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但那只会写出摹拟体的唐诗。而熟读这本《唐诗三百年》,相信不少读者,能写出时代新声的“旧体”新诗。
周松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