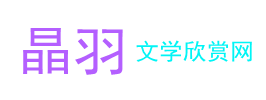将军胡同的故事有几节
不寻常的胡同(连载一)‖刘维嘉,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刘维嘉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将军胡同的故事有几节1
不寻常的胡同(连载一)
刘维嘉
通州的“十八个半截”胡同是回民聚居地胡同的统称,位于通州老城区的东南部。它在南大街的东侧,北起回民胡同,南至东顺城街,其中有北二条、马家胡同、安家大院、中街、紫竹庵胡同、白将军胡同等诸多胡同。
“十八个半截”胡同名称的由来,版本很多,其中有神话故事(九条龙传说);有民间典故(小贩到此总犯迷糊,转不出来时的感慨);有清真寺之说(回族人去清真寺礼拜,盖房时自觉留出一条中街形成了十八个半截胡同)。
曾经在回民胡同出生、成长和居住的人们,也许和我一样,深深烙下了胡同的许多印记,总会时不时地想起来吧。
一
建于元代的回民胡同,全长大约500米,东西走向,与东长安街延长线新华东街和昔日的东大街平行。胡同西边的小楼十字路口左右两侧是南大街。自十字路口一直往前是西大街。出胡同西口往右拐,途经南大街北口,过了闸桥儿十字路口再往前是北大街。从胡同的东头向左拐弯儿有五六十米长,直通新华东街。
胡同北侧曾有三条自然形成的无名小胡同,南北走向,直通新华东街,如今仅剩一条了。胡同中部的煤厂南北相通,但通行有时有晌,煤厂下班后,前后两处大门都要关上。那个煤厂早已经不存在了,原址盖了商场;胡同南侧有清真寺、安家大院等几条胡同分别通往“十八个半截”胡同的各条胡同。由此可见,回民胡同四通八达。
这条胡同的道路宽窄与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差不多,是“十八个半截”胡同最宽的胡同,与其说是一条胡同,倒不如说是一条大街。过去,此条胡同是砂石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重新铺设了污水管道,还铺设了柏油路,而其他胡同仍然是土路或砂石路。
往日的这条胡同,古老的四合院儿多、大杂院儿多、单位多、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多。此外,卖报的、卖瓷器的、卖鸡毛掸子的、理发的、修搓板的、卖香油的、吹糖人的、送牛奶的、卖蝈蝈的……从早到晚,常来胡同里忙活,其中有挑着担子的、推着车的、拉着车的、骑着车的……
“十八个半截”胡同的居民上学、上下班、购物、看电影、去公园、就医……除了南大街,回民胡同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二
回民胡同中部坐落着通县民族小学(原名“穆光小学”),始建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冬季,是由著名回族史学家、教育家、中国回教联合会通县分会委员金吉堂(1908—1978)先生创办并担任校长。1940年4月30日正式开学。后来,慈善家、万通酱园创始人、通州清真寺管事乡老马兆丰先生,特意把位于清真寺对过儿的万通酱园大部分加工厂房捐给学校,支持学校发展。
通县政协《文史选刊》第11期(1992年6月)刊登了通县人民政府督学室副主任王天信写的《民族小学沧桑》,介绍了民族小学的发展情况,其中写道:“1951年,清真寺提出申请,要求政府接管穆光小学。1952年9月,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学校……1955年,学校改名为回民小学……1957年,几位回族教师根据本校学生构成情况,建议将回民小学改名为民族小学,获得政府批准。”1955年,通县政协副主席、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委员、著名中医、家住北二条胡同的朱翊周先生被学校聘请为名誉校长。1989年,县政府又投资130万元在原北院儿校址兴建了一幢2800多平方米的教学楼,并于1990年12月底竣工并投入使用。1997年通县撤县设区后,学校改名为通州区民族小学,直至现在。
据“十八个半截”胡同的本土作家马永深(笔名马工)介绍:“乡老、知名中医朱向如(朱翊周之子)把金吉堂、马兆丰等知名人士创办‘穆光小学’的经过制成碑文,立于清真寺院内,以彰显其德,示育后人。”
通县民族小学距离我家住的大杂院儿不远,院儿里的不少孩子都是在这所小学毕业的。当年,学校分为南院儿和北院儿两个校区,都是平房,校门相对,中间隔着回民胡同。南院儿大门洞靠前的上方悬挂着刻有“通县民族小学”六个字的木质匾额,是黑底金黄色繁体字。2009年1月,我去回民胡同拍照时,拍下了南院儿的大门和这块匾额,上面显示的门牌是回民胡同66号。
当年学校南院儿有个大操场,操场西边正中位置有砖砌的长方形土台子,学校的大活动都在那里举行。院儿里有很多松树,除了家雀儿,还有其它鸟儿,常在松树间跳来跳去的。后来得知,南院儿是清真寺的房产,学校已经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退还给清真寺。
记得刚进校时,老师教我们唱了两首歌,一首是电影《红孩子》插曲《共产儿童团歌》,另一首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加入少先队那天,学校少年鼓号队演奏之后,我们站在庄严的队旗下,齐声唱起《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戴上了红领巾,并举起右手庄严宣誓。这让我从小就懂得了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要永远学习先辈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继承革命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勇敢前进。
1965年春天,我们班有几个同学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到通县礼堂参加了表彰大会,观看了《红孩子》这部电影。
几十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唱过的队歌和老师的教导,每当听到鼓号队的鼓号声,总会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加入少先队以后,我们经常参加各种活动。星期天,我们小队长佩戴着“一道杠”,举着红色小队旗,带领我们排着队去县天文馆参观;到通州烈士陵园缅怀先烈;聆听老红军、老八路和志愿军英雄讲述革命故事;去鼓楼看小人儿书、玩儿游戏;到东关小树林子抓蚂蚱、听鸟儿叫,还去运河边抓小螃蟹,尽情享受大自然的乐趣。
我们五年级那年,班主任梁老师号召我们结对子,就是结成“一帮一,一对红”和“多对红”,男女同学自由搭配,目的是互相帮助。上课时,有时一方忘记带铅笔,另一方就会雪中送炭;一方遇到老师留的作业不会做,另一方就在教室陪着一起做,直到完成作业。同学间也会在节假日相互串门儿,先做完作业,再一起玩儿,女同学玩儿跳橡皮筋、丢沙包、抓羊拐子,男同学玩儿弹球、抽汉奸、打尜儿,到了吃饭点都舍不得回家。
与我结成“一对红”的是个梳着大辫子、大眼睛的女同学。至今还记得那天下课后,一个女同学问我:“我的姐们儿让我问问你,她想和你结成‘一对红’,你同意吗?”我听了也没多想就说:“同意。”第二节课下课后,这个女同学又来找我,她说:“我的姐们儿说了,你的回答太简单了,是真的想和人家结为‘一对红’吗?”正说着,她的那个姐们儿也来到我的课桌前,我向她当面道了歉。我的“一对红”同学学习比我好,在学习上经常帮助我。如果有人欺负我,她从不袖手旁观。
以前,我们身体功能有障碍的人走在胡同里,总会有人指指点点,甚至说着侮辱和歧视我们的顺口溜,你干生气也白搭,都是以往流传下来的极不文明的陋习。自1991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后,随着法制宣传的不断深入,那些顺口溜便逐渐消失了。
我上小学期间,在胡同里可没少听那些扎心的顺口溜,一些顽童也肆意欺负我们。因为双腿功能障碍,我只能靠架拐行走,所以让我过早地尝到了受歧视的滋味儿,也让我过早地懂得了做人的尊严。
记得上六年级那年,我们年级从南院儿搬到了北院儿。一次下课后,有个学生用顺口溜骂我,我的“一对红”和其他同学瞅见了,纷纷指责那个学生,可他仍然骂个没完没了,还要抢夺我的拐杖。我心想:“我并不认识你,也没招你惹你。我有我的尊严,岂能容你!”于是愤怒地举起拐杖揍他,没想到把站在我身后不远的“一对红”同学的额头划破了,我当时光顾着愤怒了,也没想到向她道歉。如今已经过去50多年了,每当想起这个事儿,总觉得对不起她。
我们班的同学,绝大部分都是“十八个半截”胡同的,同学彼此间经常串门儿,与同学的长辈和兄弟姐妹也都熟悉了。
1970年底,我们从民族小学毕业了,有的被分配到通县一中、三中,还有的被分配到新成立的通县五中。同学们恋恋不舍地告别老师和学校,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没能照一张集体合影。
民族小学自建成以来,在学子的身体素质、知识学习,特别是思想品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由此不知造就了多少各行各业的人才。(待续)
将军胡同的故事有几节2
“十八个半截儿胡同”,不是通州人光是听到这名字就会犯迷糊。但是在通州的,没有人不知道南街。18个“半截儿胡同”,是通州为数不多的老旧平房区,这里住着汉、回、满、蒙古、高山族近6000名居民,其中70%是回族。
十八个半截胡同的由来
传说这里以前没有中街,只是一条条的东西向的胡同。有个算命的老道路过南大街,扬言这一条条的胡同就是九条龙,以后会有人造反。这消息很快就传到皇帝的耳中,皇帝于是下令将这九条胡同拦腰斩断,节成十八条半截胡同。
传说终归是传说。实际上是因为这些胡同回族人需要经常到清真礼拜,逐渐围寺而居形成的。中间的一条中街,使得每条胡同到达清真寺的路程减少。一条条胡同形成的时间也各有不同。十八个半截的概念大概是在民国时期形成。
中街两侧的胡同原本也是有着各自的名字,从北至南分别是,北二条胡同,回回三条,马家胡同,熊家胡同,半截胡同,紫竹庵胡同,四眼井胡同,蔡老胡同,史家胡同,白将军胡同,头条胡同,南二条胡同,南三条胡同,牛犄角胡同
最有名的清真寺,连皇帝都来过
在十八个半截胡同里有北京四大清真寺之一的通州清真寺。通州清真寺创建于元代,民间有元代回民遍天下的说法,可是通州的回民并非始于元代,应该起于辽代,并居住在于家务、枣林庄一带。
清康熙年间,圣祖曾来到此寺,于是就有了邦克楼门额楷书“万寿无疆”木匾。通州清真寺历史悠久,建筑别致,是历史名镇的重要见证,也是运河历史的一段真实写照。
门口的烫金匾额格外醒目。步入院内,雕梁画栋随处可见,大殿外数十根金柱涂着朱漆绚丽夺目,柱上的缠枝牡丹则玲珑精美。
传说中的牛市口
“牛市口就在这儿,年过古稀的老人应该都知道,年轻人知道的不多。随着漕运兴盛,贸易繁荣,回民在附近聚居,渐成街巷,形成了牛市胡同,牛市胡同的西口称牛市口。
名人也住过十八个半截
历史上,住在“十八个半截”的名人不在少数,大名鼎鼎的白镕白将军居住过着儿,所以才会有白将军胡同。除了白镕,白将军胡同还住过另一位将军,就是爱国将领冯玉祥。
这些胡同承载了多少欢笑。夏天孩子们成群结伙的藏猫儿,拍蛐蛐儿,西海子树林里拔根儿。这些都是咱们童年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今天我们就好好认识一下这大名鼎鼎的“十八个半截儿”。
整理自网络
将军胡同的故事有几节3
胡同,滥觞于元,经八百余年传承至今,是北京城的脉搏,是北京历史与文化的载体,亦是联结这座五朝古都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不少著名作家,例如季羡林、汪曾祺、赵大年等人,有的在胡同中居住了数十 年,有的则只是于胡同中短暂居住,对胡同有着不同的看法与感情。在他们笔下,北京的胡同生活各具风情。
季羡林 |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小胡同也爱我,我们已经结下了永恒的缘分。
六十多年前,我到北京来考大学,就下榻于西单大木仓里面一条小胡同中的一个小公寓里。白天忙于到沙滩北大三院去应试。北大与清华各考三天,考得我焦头烂额,筋疲力尽。夜里回到公寓小屋中,还要忍受臭虫的围攻,特别可怕的是那些臭虫的空降部队,防不胜防。
但是,我们这一帮山东来的学生仍然能够苦中作乐。在黄昏时分,总要到西单一带去逛街。街灯并不辉煌,“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也会令人不快。我们却甘之若饴。耳听铿锵清脆、悠扬有致的京腔,如闻仙乐。此时鼻管里会蓦地涌入一股幽香,是从路旁小花摊上的栀子花和茉莉花那里散发出来的。回到公寓,又能听到小胡同中的叫卖声:“驴肉!驴肉!”“王致和的臭豆腐!”其声悠扬、 深邃,还含有一点凄清之意。这声音把我送入梦中,送到与臭虫搏斗的战场上。
将近五十年前,我在欧洲待了十年多以后,又回到了故都。这一次是住在东城的一条小胡同里:翠花胡同,与南面的东厂胡同为邻。我住的地方后门在翠花胡同,前门则在东厂胡同,据说就是明朝的特务机关东厂所在地,是折磨、囚禁、拷打、杀害所谓“犯人”的地方,冤死之人极多,他们的鬼魂据说常出来显灵。我是不相信什么鬼怪的。我感兴趣的不是什么鬼怪显灵,而是这一所大房子本身。它地跨两个胡同,其大可知。里面重楼复阁,回廊盘曲,院落错落,花园重叠,一个陌生人走进去,必然是如入迷宫,不辨东西。
然而,这样复杂的内容,无论是从前面的东厂胡同,还是从后面的翠花胡同,都是看不出来的。外面十分简单,里面十分复杂;外面十分平凡,里面十分神奇。这是北京许多小胡同共有的特点。
据说当年黎元洪大总统在这里住过。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北大校长胡适住在黎住过的房子中。我住的地方仅仅是这个大院子中的一个旮旯,在西北角上。但是这个旮旯也并不小,是一个三进的院子,我第一次体会到“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境。我住在最深一层院子的东房中,院子里摆满了汉代的砖棺。 这里本来就是北京的一所“凶宅”,再加上这些棺材,黄昏时分,总会让人感觉到鬼影憧憧,毛骨悚然。所以很少有人敢在晚上来造访。我每日“与鬼为邻”,倒也过得很安静。
第二进院子里有很多树木,我最初没有注意是什么树。有一个夏日的晚上,刚下过一阵雨,我走在树下,忽然闻到一股幽香。原来这些是马缨花树,树上正开着繁花,幽香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这一下子让我回忆起十几年前西单的栀子花和茉莉花的香气。当时我是一个十九岁的大孩子,现在成了中年人。相距将近二十年的两个我,忽然融合到一起来了。
不管是六十多年,还是五十年,都成为过去了。现在北京的面貌天天在改变,层楼摩天,国道宽敞。然而那些可爱的小胡同,却日渐消逝,被摩天大楼吞噬掉了。看来在现实中小胡同的命运和地位都要日趋消沉,这是不可抗御的,也不一定就算是坏事。可是我仍然执着地关心我的小胡同。就让它们在我的心中占一个地位吧,永远,永远。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小胡同也爱我。
汪曾祺 | 古都残梦——胡同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胡同的繁体字是“衚衕”。为什么叫作“胡同”?说法不一。多数学者以为是蒙古话,意思是水井。我在呼和浩特听一位同志说,胡同即蒙语的“忽洞”,指两边高中间低的狭长地形。呼市对面的武川县有地名乌兰忽洞。这是蒙古话,大概可以肯定。那么这是元大都以后才有的。元朝以前,汴梁、临安都没有。
《梦粱录》《东京梦华录》等书都没有胡同字样。有一位好作奇论的专家认为这是汉语,古书里就有近似的读音。他引经据典,做了考证。我觉得未免穿凿附会。
北京城是一个四方四正的城,街道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北京只有几条斜街,如烟袋斜街、李铁拐斜街、杨梅竹斜街。北京人的方位感特强。你向北京人问路,他就会告诉你路南还是路北。过去拉洋车的,到拐弯处就喊叫一声“东去!”“西去!”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儿!”
沟通这些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街道的,便是胡同。胡同把北京这块大豆腐切成了很多小豆腐块。北京人就在这些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里活着。北京有多少条胡同?“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
胡同有大胡同,如东总布胡同;有很小的,如耳朵眼儿胡同。一般说的胡同指的是小胡同,“小胡同,小胡同”嘛!
胡同的得名各有来源。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如手帕胡同,当初大概是专卖手绢的地方;头发胡同大概是卖假发的地方。有的是皇家储存物料的地方,如惜薪司胡同(存宫中需要的柴炭),皮库胡同(存裘皮)。有的是这里住过一个什么名人,如无量大人胡同,这位大人也怪,怎么叫这么个名字;石老娘胡同,这里住过一个老娘——接生婆,想必这老娘很善于接生;大雅宝胡同据说本名大哑巴胡同,是因为这里曾住过一个哑巴。有的是肖形,如高义伯胡同,原来叫狗尾巴胡同;羊宜宾胡同原 来叫羊尾巴胡同。有的胡同则不知何所取意,如大李纱帽胡同。有的胡同不叫胡同,却叫作一个很雅致的名称,如齐白石曾经住过的“百花深处”。其实这里并没有花,一进胡同是一个公共厕所!胡同里的房屋有一些是曾经很讲究的,有些人家的大门上钉着门钹,门前有拴马桩、上马石,记述着往昔的繁华。但是随着岁月风雨的剥蚀,门钹已经不成对,拴马桩、上马石都已成为浑圆的,棱角线条都模糊了。现在大多数胡同已经成为“陋巷”。胡同里是安静的。偶尔有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来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响)的声音,算命的盲人吹的短笛的声音,或卖硬面饽饽的苍老的吆唤— —“硬面儿饽——阿饽!”“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时间在这里又似乎是不流动的。
胡同居民的心态是偏于保守的,他们经历了朝代更迭,“城头变幻大王旗”,谁掌权,他们都顺着,像《茶馆》里的王掌柜的所说:“当了一辈子的顺民。”他们安分守己,服服帖帖。老北京人说:“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真是北京人的非常精粹的人生哲学。永远不烦躁,不起急,什么事都“忍”着。胡同居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蒸一屉窝头,熬一锅虾米皮白菜,来 一碟臭豆腐,一块大腌萝卜,足矣。我认识一位老北京,他每天晚上都吃炸酱面,吃了几十年炸酱面。
喔,胡同里的老北京人,你们就永远这样活下去吗?
赵大年 | 胡同文化的韵味
几年前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陈建功和我骑自行车沿着东皇城根这条热闹的小街往北走,要选一条胡同,为我们合写的京味小说《皇城根》“定位”。
每逢散步或骑车钻进小胡同,不论哪条胡同,我都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
今天略微不同,路牌上写着“黄城根”,哈,这简直是笑话,北京的城墙有紫的,灰的,哪儿来黄色的城呢?只有皇城!对啦,甭说中外游客,就是北京的许多年轻人,也不知道皇城在哪儿,还以为就是紫禁城呢。历史上,不,也许不该说是历史,本世纪内北京还有四重城: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 拆啦,虽说拆有拆的道理,却令酷爱北京的吴晗、梁思成们痛心疾首。如今只剩下皇城根这地名,还被忌讳“皇”字的人改写为“黄”,莫非这里不是六百年帝都?……唉,我这北京人逛北京,爱家乡,对卢沟桥上的石狮子也会如数家珍的呀。
我们找到了翠花胡同,正合心意——故事就应该发生在这样的胡同里——那位从未出场,却令一代名医金 一趟神魂颠倒、抱憾终身的姑娘就叫翠花。这是我们心里的胡同啊。它的东口是繁华喧嚣的王府井商业街,洋气的华侨大厦、民航大楼;在西口又抬头可见故宫冷峻的角楼和凝重的紫墙。这新旧反差极大的两片天地之间,二百米长的小胡同里居住着地道的北京老百姓,小说里的主人公,他们顽强地保存着北京人的脾气秉性。
有人说,中国最洋气和最传统的建筑物都在北京。当然不光是房子,还有观念、文学、艺术、民风……说到底,还是人。北京人得天独厚,生活在全国的文化中心。有趣的是,大部分北京人又住在小胡同里,创造和维系着深厚的胡同文化。前辈作家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龙须沟》植根于胡同文化, 今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北京城,我们要写《皇城根》,同样得益于胡同文化。
小胡同、四合院是这种文化的载体。我们把小说的环境“定位”在胡同里,写起来就得心应手,如鱼得水。北京人特讲仁义。我们把翠花胡同更名为仁德胡同,让老中医金一趟住在这里,他有祖传的“再造金丹”,给宋庆龄、郭沫若、江青看过病,只需来一趟,药到病除,所以许多大人物慕名而来,应接不暇。但他每星期都抽出一天来给街坊邻居看病,遇到穷苦人还免费义诊。不是说在商品大潮冲击下就认钱不认人了吗?不,仁德胡同还保留着一片净土。这种温馨的、助人为乐的邻里关系,还在北京众多的小胡同里顽强地保存着。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样的燕赵悲歌,在两千多年以后《四世同堂》的小胡同里不是还能听得见吗?在勇敢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祁老太爷等平民百姓身上,都能看到北京人这种不畏强暴的正义感。
然而,北京城的确在飞速地变化着。我们的小说应该是一面镜子,瞧,靠自家人支撑的“金一趟诊所” 也分化了:金秀委曲求全,还苦撑着,谁叫她是长女呢?义子兼女婿的张全义却有了外遇。小女儿金枝向往外面的世界,成了家教和家规的叛逆。最后固守在金府的大概只剩下金一趟本人和那位比金家 人还姓金的五十年义仆杨妈。《皇城根》这本小说和同名电视剧,也许仅仅是个象征,记述着北京人大踏步前进当中的艰难痛苦,就像生我养我的小胡同、四合院正在被雨后春笋般的高楼大厦无情取代一样。
北京的小胡同是与巍峨的天安门,金碧辉煌的故宫,上百所高等学府和上百个大使馆交织在一起的。“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您不论从哪条胡同里,要请出几位书画家、名角、票友、 学者、教授,或者部长、将军,都不困难。这里乃藏龙卧虎之地。当然,胡同里的小人物更多。好在北京人特宽厚,不论职位高低皆可称爷。小小年纪的贾宝玉是宝二爷,老妓女赛金花是赛二爷,二道贩子是倒爷,蹬平板三轮的是板儿爷,暴发户是款爷,和尚道士是陀爷,耍嘴皮子的是侃爷,连那背插小旗儿的泥塑玩具也是兔儿爷。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这么多老少爷们儿,远的不说,自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谁家没有悲欢离合?哪条胡同里没有五车故事?在我们写小说的文人心目中,这些故事既然发生在北京,就必然与国家兴衰、民族荣辱紧密相连,要是写得好,它应该是北京韵味浓郁的作品。
我不知道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北京还能保留多少小胡同?但我相信,这种胡同文化和它浓郁的京华韵味,将长期保存在文学艺术和人们的心里。
·End·
本文节选自《胡同的故事》
出版社: 低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 ◆ ◆ ◆
本文为北大公共传播转载
版权归作者所有
编辑 | 马婷
欢迎合作 | 投稿
pcsdpk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