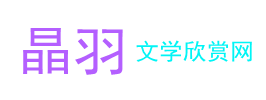对照式的故事有哪些
文学与帝国:殖民阶序的多重面孔,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澎湃新闻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对照式的故事有哪些1
李雅雯
文学在全球政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时值俄乌危机,江弱水老师在“神话的去魅与解毒”一文中论证了俄国文学是如何在俄国领土扩张的过程中合法化其侵略者的主体身份的。援引波兰裔美国学者埃娃·汤普逊(Ewa Thompson)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他指出许多聚焦对内部镇压反抗的俄国文学在无形中也让俄国对外的扩张“消失”在视野。在此文中,笔者打算进一步延伸对于文学与帝国意识的讨论,扩充一些方向和例证,希望能够对于辨认和抵抗帝国意识和殖民逻辑在当下的复现有所助益。
《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
深入“荒蛮之地”:知识生产和殖民阶序的建立
许多殖民时期的书面作品都围绕“深入‘荒蛮之地’”(“going native”) 这一主题展开。“native” (原住民的,当地的)在西方人类学的历史脉络中从来都不是一个脱离政治的中性词。殖民时期,不论是前往殖民地的人类学者,进行民族志记录的社会学者,做生物和地质考察的“探险”家,亦或是寻找“灵感”的艺术家,作家,还有传教士,他们的书写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地印证了帝国秩序和殖民逻辑。在这一逻辑中,被殖民者或者原住民群体成为了和处于帝国中心的欧洲白人截然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原始”“低等”“野蛮”的“有色”人种。
但实际上,他们所印证的不过是一种能够前往所谓的“荒蛮之地”的行动的特权和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传播“客观”知识和“普世(适)”文化的话语霸权。殖民统治和话语生产两者相辅相成,建立了一整套以否定被殖民人群的生物特征和本土文化为基础的种族主义殖民秩序,进而维系了西方中心式的现代文明观和白人至上的殖民统治。欧美白人成为了 “文明”与“进步”的代言人,“白皮肤”与西方价值观和世界观也成为了衡量“高等”和“高级”的标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黄皮肤,棕色皮肤,黑皮肤及其代表的文化的劣等性。
为殖民统治正名的帝国逻辑,以及对于被殖民人群的负面建构,牵涉了知识和文化生产的方方面面,并且并没有随着被殖民地区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消失,而是以更加隐晦的形式在当今世界存续。被殖民的人群也会内化对于自身的种族主义叙事,被迫甚至主动顺从殖民权力秩序和话语体系,而这些叙事也仍然在影响着前殖民地独立后的民族想象和国家建设。
比如在去年上映的、根据弗兰克·赫伯特1965年的同名作改编的科幻电影《沙丘》中,厄拉科斯星球的原住民弗瑞曼被广泛认为以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为原型。其中有一幕,公爵的儿子保罗和杰西卡夫人即将进入沙虫的领地,保罗建议他们模仿弗瑞曼人的行走姿势。他说:“我们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死定了。我们必须得像弗里曼人那样行走。这就是所谓的沙步。”而这一幕与法国生理学家、民族志电影导演菲利克斯·路易·雷格诺(Félix-Louis Regnault)在19世纪末对于西非人行走步态的“非正常”性的描述不谋而合:雷格诺认为西非人高度弯曲、“野人 ”、“史前人类”的走路方式,有助于法国士兵行军。
文学曾一度被认为是一种远离政治的艺术形式,着眼于微观和独特的个人而非宏大和广义的集体,某种理想的避难所和慰藉性的存在。这种思维定式使得文学中对于被殖民和少数族群的非正义构想更难以察觉。
在非洲文学奠基者,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的笔下,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代表作《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无疑坐实了对一些文学作品与殖民主义的合谋的担忧。阿契贝认为,康拉德美学化了“深入‘荒蛮之地’”这一主题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殖民秩序。这本极具感染力的书所传达的逻辑是,已经 “克服”了前现代黑暗的欧洲现代文明(以贩卖象牙的英国人库尔兹为代表),在接触到非洲这片“前现代”“黑色大陆”(在书中以刚果为代表)后,面临着被“野蛮”再度吞噬,重新回到黑暗的危险(库尔兹的染病和死亡)。
阿契贝指出,用“作者不等于叙述者”这一点来反驳康拉德是种族主义者这一事实是孱弱的。研究《黑暗之心》的西方学者常常会说,康拉德关注的不是非洲,而是欧洲人人性的退化,故事的重点是讽刺欧洲在非洲的“文明使命”(civilising mission),刚果只是库尔兹人性瓦解的一个背景。阿契贝则认为,“非洲作为环境和背景……作为一个形而上的战场”正是问题所在:在书中出现的非洲人没有任何可辨识的人性,“难道没有人察觉到,这样把非洲降格为一个欧洲人人性分裂的道具,是多么荒谬,反常,以及傲慢吗?”
承认文学和艺术对于帝国维序所扮演的共谋作用并不等同于拒绝作品和作家本身,而是看到艺术和政治的亲缘性,警惕艺术作品中所默许的、正当化的甚至浪漫化的不正义的权力关系,以及最重要地,消解这种逻辑在现实世界对于处在权力被剥夺、秩序受制方的人群可能造成的伤害。正如新闻界需要交叉核查多处信息源,后殖民思想家爱德华·萨义德提倡一种“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呼吁我们倾听前殖民地本土作家和前宗主国少数族裔作家的声音,进而反思我们长久接触的知识、文化和艺术生产者所构筑的世界是“谁”的世界?以“谁”为主体的世界?其主体意识的显现是否伴随着,甚至基于对于某些他/她者的去主体化、非人化和噤声?
两种流亡: “普世”的异化感与人类境况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和阿西亚·杰巴尔(Assia Djebar)都是阿尔及利亚人,都用法语写作,但他们的背景和观点截然不同。加缪是法国定居者的后代,包括加缪在内的大多数法国定居者都反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加缪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法国。他笔下的人物经常觉得自己与阿尔及利亚格格不入,但他们也没有其他的家。他们意识到自己在殖民统治下的不公平特权,但他们也对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保持警惕,更无法想象在帝国之外还有什么更公正的方式来组织阿尔及利亚社会。杰巴尔是一名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有着阿拉伯和阿马兹格背景。阿马兹格人有时被外人称为柏柏尔人,是北非的一个原住民群体。作为一名年轻女性,她积极参与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她的著作涉及独立战争、法国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以及阿尔及利亚妇女正在进行的平权运动。对位阅读杰巴尔和加缪的两个选集,《阿尔及尔妇女在她们的公寓里》(1980)和《流放与王国》(1957),我们能从杰巴尔本土阿尔及利亚的视角感受到她对加缪作品中隐含的、想当然的或否认的内容做出的挑战。
阿尔贝·加缪
加缪经常被解读为一个关注人类的生存境况的普世性作家。他在1957年,也就是《流放与王国》出版的同一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收获的评委题词认为“他的重要文学创作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时代关于人类良知的问题”。可以看出,加缪所描绘的人物常常被放到人类本身这个大的范畴里。
而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指出,加缪虽然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策持批评态度,也并不是帝国主义的拉拉队,但是他反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这排除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其他群体,包括阿马兹格人和犹太人,但尤其是法国人。萨义德认为,加缪实际上是不希望阿尔及利亚由占大多数的阿拉伯穆斯林来统治,如果阿尔及利亚选择民主解决方案就会由阿拉伯穆斯林治理,而不是占少数的法国人。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萨义德的批评,重要的是他不是简单地以这些理由否定加缪的作品。萨义德肯定了加缪的写作风格和技巧,但同时提出,我们需要把创作背景和内容本身放在一起思考,即必须在思考加缪的主题的同时思考他的政治立场,这种方式将丰富我们对文本的理解。
《流放与王国》
《流放与王国》(Exile and Kingdom)中的很多故事都设定在阿尔及利亚,但叙事都是单一的法国定居者视角,阿拉伯人被无形中背景化和消声。其中,“不贞的妻子”更是把政治性的赋能,即对于阿尔及利亚土地的复魅,编织进了法国定居者女性摆脱家庭束缚,重获自由的女性赋能中。故事写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前后,女主人公Janine虽然在阿尔及利亚出生长大,但她对于陌生的阿拉伯语而感到非常沮丧。从她带有殖民色彩的字里行间里我们可以读出她对于即将“失去”的土地的悲伤,同时对真正意义上占有土地的强烈渴望。故事的最后,Janine和土地实现了交融(即标题的“不贞”的来由),获得了与丈夫的家庭生活中得不到的满足,同时也与这片让她感受到陌生的土地达成了和解。
杰巴尔的短篇“无所谓流放”(“There is no Exile”),同样写于独立战争前后, 在标题和内容上都与加缪的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故事中的无名叙述者被多重不同的结构所禁锢,因为战争被迫从故国阿尔及利亚流亡到突尼斯,同时女主人公则依然被限制在公寓里,被家人逼婚。在这里,流放并没有带来解脱,结构性的压迫不会因为地理流动而消失,殖民和传统社会的双重压迫意味着没有和解可言,反抗是唯一的出路。
《阿尔及尔妇女在她们的公寓里》(Women of Algiers in Their Apartment)这一标题来自法国著名画家德拉克洛瓦1834年的同名画作,集子中的另一篇《受禁的目光,戛然而止的声音》(“Forbidden Gaze, Severed Sound”)也直接批判了德拉克洛瓦的东方主义男性凝视。穆斯林传统住宅哈勒姆(harem)作为女性的私人空间通常不允许男性进入,德拉克洛瓦却被允许凝视这些穆斯林女性,并将描绘她们的画作在法国展出,使其他欧洲人也拥有了这样凝视阿尔及尔女性的特权。杰巴尔所抨击的正是这样一种暴力的表征:德拉克洛瓦从窥视当地女性以及她们的沉默中获得了快感和灵感,并把她们作为奇观在殖民宗主国之间展出。杰巴尔同时也批评了本是同盟和战友的阿尔及利亚男性:虽然女性为独立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参战和用身体做掩护去放置炸弹,但在战争结束后,她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改变。
《阿尔及尔妇女在她们的公寓里》
我们需要能够同时思考法国定居者女性体验到与异化的殖民土地达成和解的时刻,以及阿尔及利亚的女性作为自杀式炸弹携带者用她们的身体抵抗殖民统治的时刻。回到萨义德说的对位阅读,加缪和杰巴尔笔下的法国定居女性和阿尔及利亚当地女性截然不同的境遇需要我们将来自(前)宗主国的作家与(后)殖民地的作家相互联系起来阅读,并反思加缪的普世人类境况是否真的那么普世?
天性使然?政治性和社会化的心理失调
在“特殊情况”常态化以及公共讨论空间紧缩的当下,想必“政治性抑郁”这一概念对我们不算陌生。近年出版的书写性侵的文学和回忆录也提醒着我们需要在更大的社会环境和(多重)结构性压迫中看待个人的心理创伤。但是在西方早期(甚至是今天)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学界,很多心理学家倾向于认为个人与社会是分离的,个人的问题是由个人生活中的某个特定事件或只与个人有关的特定环境造成的,对心理失调的归因往往局限在个人维度。
而在殖民地,殖民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压迫对于个体心理失调所扮演的角色非但没有被纳入考量,被殖民个体的精神问题甚至会招致整个族群的病理化,并被进一步用来佐证殖民统治的正当性。比如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阿尔及尔精神病学派创始人,法国精神病学家安托万·波洛(Antoine Porot)把北非的阿拉伯人本质化为一个在生物学上与欧洲白人完全不同的独立的人类类别。伯纳德·多雷(Bernard Doray)在他2006年出版的《尊严:乌托邦的失败》(La Dignité: les debouts de l'utopie)一书中写到,“贯穿这些所谓‘科学’著作的想法非常单一:‘当地人’臭名昭著的病态冲动是其种族生物缺陷的体现,因为他们没有像自豪的欧洲人大脑那样柔软的皮质”。
法国哲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奥克塔夫·曼努尼(Octave Mannoni)专门研究了马达加斯加的殖民心理学并在1947年出版了《普罗斯佩罗与卡立班:殖民心理学》(Prospero and Caliban:The Psychology of Colonization)。他宣称,马达加斯加人有依赖性人格类型(dependence complex),这种人格促使马达加斯加人寻求可以依附和服从的上级权威或者主人,从而缓解对于独自生存的恐惧,因为他们无法应对变化,他们的传统文化也不强调个体的独立。曼努尼断言马达加斯加人的这种人格类型使得殖民主义在马达加斯加顺理成章地发生。与波洛的生物本质论相比,曼努尼认为文化决定了人格,而马达加斯加人“固有的”依赖性人格使得殖民主义变成了一种需要。
可以看出即使是像心理学、医学这样被普遍认为“客观”或与政治脱离的学科,也深深地嵌入了殖民结构,与关于生物和文化差异的种族主义思想携手并进,忽视了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社会失调是造成个人和心理失调的重要成因。
马提尼克反殖思想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其1952年出版的著作《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中对这种把个人与社会和政治剥离的看法做出了强有力的抨击。这本书最初是法农在法国里昂大学接受精神病学训练的博士论文,从它作为论文被拒绝接收可以看出法农的想法和政治框架与当时相关学科的主流学术范式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本书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指出了殖民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殖民主义也以欧洲白人作为参照系搭建出了一整套对于人性的判定标准,其中隐含的信息便是,不符合这些标准的族群便不够“人”甚至“非人”,比如肤色不够浅,英语有口音,不具备读写能力,精神不健全,“天生”暴力,以及如曼努尼所说,“天性”依赖,所以以“文明教化”名义而实行的统治和压迫是“正当”的。
在一个系统地贬低黑人的殖民体系中,一些黑人被逼着试图适应和主动顺应殖民者的文化,以试图获得接受,并通过“努力”来减少某些方面的种族主义偏见。法农相当同情戴上这些“白面具”以寻求种族主义的殖民体制认可的被殖民者,但他也很清楚,这隐含着对这个体制以及对把被殖民群体非人化的逻辑的肯定。黑人或被殖民者应该通过颠覆制度来寻求人性,而不是在这个秩序内部努力攀升,以妥协的方式扭转他们的人性被异化的状态。
法农指出了曼努尼的论调根本上的逻辑颠倒,他提出即使马达加斯加人有这种依赖型的人格,也是由殖民主义造成的。在出版于1961年的《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一书,通过多个具体的阿尔及利亚案例,法农再次强调阿尔及利亚人被本质化的暴力倾向是殖民主义的产物而非促成殖民统治的条件。
法农提出的关键性问题是,在一个病态的世界里,个人能够独善其身,实现自我解放吗?法农认为,个人的精神健全和愈合与治愈病态的社会是密不可分的。从病态的个人引伸到病态的社会,而治愈个人则必须治愈社会,在这一点上,法农和鲁迅对于政治性、社会化的精神病理的探索似乎有许多共通之处,虽然前者直接解构殖民话语,而后者则更注重对于传统文化压迫逻辑的揭露。
齐西·达兰加姆巴
罗德西亚(前津巴布韦)作家齐西·达兰加姆巴(Tsitsi Dangarembga)的半自传小说《不安的状态》(Nervous Conditions)是将法农的理论诉诸于文学的一次重要尝试,并引入了被法农忽视的性别视角。题目取自萨特为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所作序言的一句话。主人公Tambu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全家基本都用本土语言绍那语(Shona)交流,兄弟Nhamo的突然死亡使得Tambu得以接替他,前往叔叔Babamukuru经营的教会学校上学。Tambu和Babamukuru的女儿,即她的表姐妹Nyasha成为了亲密的朋友,直到Tambu获得了一所著名教会学校学习的奖学金,从此专注于学习,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与Nyasha联系。当Tambu回家时,发现Nyasha患上了厌食症,瘦了很多,身体很虚弱。在最后一部分,Nyasha非常清楚地将她的饮食紊乱与在津巴布韦后殖民教育中的挣扎和殖民制度联系起来。
食物成为了与殖民主义同化的叙述性隐喻。达兰加姆巴在书中隐射,殖民地以及后殖民国家,由于殖民遗产在意识形态和体制上的延续,女性遭受着殖民和父权结构的双重殖民(double colonisation)。当地在殖民主义之前就存在着父权制结构,但由于殖民统治,个体遭受的不公正往往只能向内(本族)寻找泄口,于是家庭内部的暴力变得更加严重和突出。Babamukuru是殖民地黑人精英的代表,虽然自己因为殖民体系而痛苦,但他拼命地通过戴上“白面具”,“凶猛地吞噬英语字母……” 而寻求认可。而作为父亲的Babamukuru迫使Nyasha也戴上“白面具”,使其完成“盎格鲁/英国化”(anglicisation)的转变 。而Nyasha对于双重殖民的反抗则以拒绝进食的形式呈现,拒绝以放弃自己(语言和本土文化)来追寻一种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同化。
档案的沉默
努贝斯·菲利普(M. Nourbese Philip)的诗集《宗!》(Zong!)则关注档案的沉默,以及如何在空白之上构筑意义,又或者说,菲利普希望传递的是,沉默不需要创造意义,认识到语言和文字在为无端暴力辩护和构建意义中的共谋或许便是沉默的意义。
诗集标题取自千千万万从事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船中的一艘“宗”号船。或许“三角贸易”这个名称更为我们所熟知:货物,特别是枪支弹药和工厂生产的货物,被从欧洲运到非洲,在那里出售;满载着受奴役的人的船被运过大西洋,把他们卖到美国、加勒比海和南美洲去当奴隶,换取糖、咖啡等;满载美洲产品的船随即返回欧洲。
“宗号船大屠杀”(“The Zong Massacre”)发生在1781年11月29日到12月1日的三天时间里。通常情况下,穿越大西洋需要六到九周的时间,“宗 ”却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在屠杀发生之前,已经有62名受奴役的人和几名船员由于营养不良和疾病以及船上的恶劣条件而死在了船上。随着饮用水的耗尽,船长卢克·科林伍德病重,船员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把一些受奴役的人扔到海里,这样他们就可以要求保险方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他们的行为是为了“保护”一些被保险的 “货物”,即剩下的受奴役者的安全。
奴隶船(1840),J. M. W. Turner,灵感来自宗号船大屠杀。
当“宗”号船最终抵达牙买加,随后返回利物浦后,船的主人向保险公司索赔“损失”,即他们谋杀的受奴役的人,而保险公司则在拒绝赔偿后被告上法庭。陪审团判决保险方应该赔偿,后者则要求上诉并进行重新审判。结果是,只要是基于挽救经济损失的考量,即支持其他“货物-受奴役的人”的存活,商人即使是故意杀害受奴役的人也是合法的,保险公司必须赔偿。而这个屠杀事件唯一的记录就只有这一纸支持奴隶制的法律文件(Gregson v Gilbert 1783),里面充满了对受奴役者非人化的描述和对于某些情况下谋杀受奴役的人的合法性的辩护。
《宗!》正文部分的文字全部取自于这份法律文件,但通过拆解词语,填入空白,阻断意义的发生,菲利普揭示了该法律文件的荒谬性和其中骇人听闻的暴力逻辑。通过让读者努力拼凑碎片,倾听沉默的律动,对繁复的语言进行破译的尝试,菲利普希望能够引领读者去体认——哪怕只有一瞬,哪怕程度非常微小——受奴役者在船上与说着同样语言的群体区隔开,被听不懂的语言吼叫着跳海的恐惧感。
在诗集的结尾有一篇创作谈,菲利普分享了她在创作中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尴尬的悖论,即像“宗号船大屠杀”这样缺少档案(更别说从受奴役者视角出发的)记录的事件是无法被讲述的,但暴力又正因为档案的沉默而得以不被挑战地存续,因此它无从“(从受奴役者视角)讲述”,必须“被讲述”(“There is no telling the story: It must be told ”)。
在 “维纳斯双幕剧”(“Venus in Two Acts”)中,赛蒂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表达了相似的忧虑,“有可能从‘话语的不可能之处‘构建故事,从废墟中复活生命吗?……我们能如何重访‘服从的场景’而不去复制其暴力的语法?” 哈特曼提出了一种“批判性虚构”(critical fabulation)的写作方法:“通过摆弄和重新排布故事的基本元素,重新呈现不同故事和对立视角下的事件顺序,我试图影响事件的地位、撼动已被接受的或权威性的说法,从而想象曾经可能发生、可能说过、可能做过的一切。通过动摇 ‘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的客观性,及充分利用‘史料透明度’ 如何支撑历史的虚构性,我希望展示廉价而可弃的生命是如何(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历史学科中)被生产出来的,并透过想象或者倾听商品的低语、誓言和呼喊,来描写‘物的反抗’”。
通过菲利普和哈特曼的作品,虽然我们不能让受奴役者复活发出声音,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去停止想象他/她们的声音,即使这些想象本身的开展即宣告了潜在的失败。正如哈特曼所说,对一个更自由的未来的设想需要我们了解档案的沉默和暴力,需要我们 “去想象不能被证实的事情”,“逼近不可说与不可知的边界”,“正视那些在消亡的瞬间才勉强可见的易逝生命”。
对文学作品中的殖民和反殖思想进行反思有助于我们及时警惕当代文化中涌现出的殖民思潮。我们可以思考,在时下在国内流行的祝福和喊话视频中付费征用(通常是半赤身裸体的)非洲黑人,并要求其演绎奇观式的定制祝福的做法,是否重复了把黑人化约为他/她们一部分生理特征的种族主义和商品化逻辑?这些祝福视频的广泛传播是否使得我们对于非洲人的想象停留在他/她的深肤色以及高度性化的身体?而他/她们的情感和思想维度则被扁平化甚至完全抹去了?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对非洲人或黑人人性的充分性的否认呢?
对于文化和思想解殖的号召虽有其局限性,因为其核心任务,即培养批判意识,能否转化为具有物质或实质意义的去殖民化行动尚且存疑。伊芙·塔克(Eve Tuck)和韦恩·杨(K. Wayne Yang)在其文章《去殖民化不是隐喻》中联系北美原住民的土地问题对这一点做了强有力的阐述。笔者同意,我们不应满足于对于话语和文化的去殖民化,并且需要警惕学院空谈和体制化收编,但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
注释
本文部分文本的选择和论述参考了伦敦国王学院比较文学系在2021至2022第一学期由Justine McConnell,Anna Bernard, Sara Marzagora教授的“文学与帝国主义”(Literature of Empire)课程。
其他参考资料
江弱水,“神话的去魅与解毒——汤普逊的《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飞地,2022年2月, https://m.enclavebooks.cn/new_article.html?id=59926.
Rony, Fatimah Tobing. The Third Eye: Race, Cinema, and Ethnographic Spectacle, Illustrated edi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1996.
Achebe, Chinua. “An Image of Africa: Rac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Vol. 57, No. 1, Spring 2016, pp. 14-27. 引文由笔者翻译。
Said, Edward. “Camus and the French Imperial Experience”, in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Vintage, 1994, pp. 204-224.
Apter, Emily. “Out of Character: Camus’ French Algerian Subjects”, MLN, Vol. 112, No. 4, 1997, pp. 499-516.
Lachman, Kathryn. “The Allure of Counterpoint: History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Writing of Edward Said and Assia Djebar”,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41, No. 4, 2010, pp. 162-186.
Uwakweh, Pauline Ada, "Debunking Patriarchy: The Liberational Quality of Voicing in Tsitsi Dangarembga's Nervous Conditions",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6, No. 1, 1995, pp. 75-84.
Hill, Janice E. “Purging a Plate Full of Colonial History: The ‘Nervous Conditions’ of Silent Girls”, College Literature, Vol. 22, No. 1, 1995, pp. 78-90.
Doray, Bernard. La dignité: Les debouts de l'utopie, La Dispute, 2006. 引文由笔者翻译。
Greenwood, Emily. “Middle Passages: Mediating Classics and Radical Philology in Marlene NourbeSe Philip and Derek Walcott”, in Ian Moyer, Adam Lecznar, and Heidi Morse (eds.), Classicisms in the Black Atlant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29-56.
赛蒂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 2008) & 黄琨(译者;2020).“维纳斯双幕剧”,广东时代美术馆,2020年6月,https://www.trueart.com/news/373732.html.
普里亚姆瓦达·戈帕尔(Priyamvada Gopal) & Aseem (译者).“去殖民化与大学:全盘否定‘西方’是殖民心智的恶果”, 澎湃思想市场,2021年7月,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30130.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栾梦
对照式的故事有哪些2
作者:苏七七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前的经验是最可珍贵的,生活未被书写入侵,一气浑成,不被作为“素材”来观察与掂量,保存了最原初最真切的感知。萧耳写《鹊桥仙》时,已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写小说,也写各式各样的随笔,文化的,艺术的,历史地理的,有一种兼容并蓄又摇曳生姿的个人风格。但一直到《鹊桥仙》,她才动用了自己最珍贵的经验——故乡的,少年的,这是她的世界观与感受力的源头。而此时此刻,她有充分的阅历、思想与技巧,来梳理这个小世界的经络与纹理,少小时,她是这个小世界里一个深受宠爱的独生女儿,而追怀时,她发现自己对这个小世界的眷恋,亦如同小镇长桥的倒影,日夕相随。
《鹊桥仙》从女主人公陈易知的梦写起,“少女思春,河边一梦”,时间是20世纪的80年代。作为怀旧的对象,栖镇并不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乡村,对栖镇的怀旧,不是对自然的怀旧。位于京杭大运河主干道的栖镇,工商业的肇始远在百年之前,依托于稻米和蚕桑,水路与船运,小镇自足且并不封闭。陈易知的祖辈是船工上岸,到父亲一辈,已经对栖镇有坚定的自信自豪。读者在《鹊桥仙》里,也时时能看到对“老底子”的回顾,陈易知们的“小辰光”(小时候)和余韵犹存的“老底子”重合在一起,是这些“发小”们的情感故园,有茧子的气味,有烘青豆和刺毛肉圆的味道,远足路过的破庙,回收站拾来的诗词,街头巷尾传来的一句越剧昆曲,这物质与文化的混合物,因为是在一种缓慢节奏中逐渐团合而成的。少女陈易知入睡时听的不是晚鸦的啼叫,而是轮船的汽笛声,它不是诗词中的古代江南,是从听说的“近现代”到亲历的“当代”的江南。
这个“当代”,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少年把臂同游的发小们,青年时代四散于各自的人生道路,去了省城,去了北京上海,去了深圳香港,去了美国新西兰,等到结婚生子经济稳定各有安身立命之处时,方明白自己是幸运的一代,不甚用心地就领受了时代的馈赠。他们重聚于栖镇河边,“荡发荡发”,随便走走,随便聊点什么。荡发,就是很去中心的一个词,自由,发散,漫无目的,就像是“内卷”的反义词。
这个词在小说里出现的次数极多,而且整个小说,也有着同样的“荡发荡发”的风格,经行之处,出来一个人物,出来一个故事,而又在岁月流逝之中,时隐时现,彼此交织映照。在这种荡发里,有一种独特的亲密感——人与环境之间有深深情感,人与人之间亦有深深情感,儿时照片中的四个人,陈易知、何易从、靳天、戴正,和他们的朋友们恋人们家人们,组成了一个如同大观园般的世界。
与现代主义之后的小说习惯于表达个体的孤独与个体间的疏离不同,《鹊桥仙》从《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这样的文学传统而来,在共同的“风俗”之中,也即一种物质与文化的语境之中,达成一种从生活习惯到身体距离的彼此亲昵。这种亲昵不完全因为爱情与情欲,比如小说中的何易从,他从小镇的中学出发,杭州读本科,北京读硕博,然后去了美国,娶妻生女,是上一代小镇做题家的范本,他与妻子小简之间是从大学同学到夫妇,一路互相扶持,也是模范夫妻,但这个人物却总在回小镇时,与陈易知,与沈美枝,有着牵丝扳藤的纠葛。或者说,在这个小说,何易从与陈易知,与沈美枝,都有一种没有边界的亲昵,这种亲昵是前现代的,就像贾宝玉与姐姐妹妹们都亲昵一样。栖镇,如同大观园,如同有一个结界,在此之内既存留着纯真的少年情怀,又容许着更模糊的身体与道德边界。
在这样的写法中,往往容易在作者的认可与读者的认可中产生缝隙,如宝二爷的何易从,如琏二爷的靳天,在小说文本所设置的语境内是自洽的,是被认可的,但读者能认可吗?在我的阅读体会里,作为男一女一的陈易知何易从,是不怎么有主角光环的,陈易知,成年后的部分流于平庸,按作者萧耳的说法,“知识分子人格束缚了她”;何易从,从小时候的孤僻性子到中年后的宝玉人设,缺乏一个让读者认同他的铺垫。他们之间没有宝玉与黛玉式的“心心相印”,易知的倾慕里,更多的是自我投射,易从的领受里,更多的是对红颜知己的相酬,他们之间的情感偏向于精神,但却缺乏足够的精神高度。但对于作者来说,这个精神高度某种意义是被有意克制的,她把栖镇少年们的成年生活写得更为现实主义。小说以青梅竹马的少年时光为底色,好感与试探里都尽是草长莺飞的青春气息,而长大成人后的情欲纷纷,不是在婚姻生活走向枯索,就是在过于轻易中走向放纵。共通的精神世界并不是易知易从的起点与核心,也没有精神生活作为他们的救赎,这不是这个小说试图给出的方向,《鹊桥仙》在青春一梦之后,更朝着世情小说的方向走,不设立生活之上的超越性想象,而是将生活本身视为全部,表象即是意义,弱化情节的因果关系,而在时间的荡发中呈现诸种可能。
小说中最动人最饱满的故事,是靳天与许湘柳的爱情故事,码头与丝厂,桑林与乌篷船,他们热切的呼吸声里伴着运河的水声,刚刚从少年进入青年的身体,最纯粹的付出与期待,萧耳写的是江南小镇的爱情,但这样明媚的爱情是超越地域与时间的,像是从《诗经》里流传而来的。靳天这个人物似乎比何易从更有读者缘(路内的序里也说喜欢靳天这个人物),他这样最初最好的爱情,却被辜负了,于是读者总有对他的怜惜。同样,沈美枝也是个被辜负的人物,屡次遇人不淑,却总还是保持着温柔的天性。小说中有各样情事,或热烈,或婉曲,或世故,或低俗,但良人与美人的被辜负,永远是世情里最引人叹惋的篇章。
《鹊桥仙》中许多小故事,前一个故事结束时,衍生着对照着又有了一个新的故事,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在布局时的用意和点染时的灵机。从世情小说的角度上看,《鹊桥仙》把自己约束在情事的范畴里,它可以有一个更宏阔的社会背景,但时间线上没有任何重要的社会事件,能带来更多社会暗面的人物,都只是点到即止,包括陈易知丈夫厅官陆韶的下马。但小说给这个婚姻设计了个有趣的起点:他们因为都不吃猪大肠而互生好感,但最后,却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在荡发荡发之间,栖镇迅速地萧条了,只有散仙戴正,留在这里开了个茶书馆,守着这一段时光。小说的最后部分,弦鼓声声匆促,各人再次风流云散,中年时光的再聚与惬意,像是《红楼梦》里海棠结社,热闹有时,消歇有时,转眼是“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后四十回,在《鹊桥仙》里很短,只是个匆匆交代,作者不忍对她的人物下狠手。
《鹊桥仙》的独特的亲密感,会延伸到作者与读者之间,大弦嘈嘈如急语,小弦切切如私语。如果你坐在栖镇桥头听着水声看这本书,就像是听着“流言”。某种意义上,作者放弃了偏向知识分子的立场,不从批判中去寻找真相,而选择了一种更前现代的叙事方法,从故事中寻找真实,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
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这些人,它们需要在叙事中得以超越时间存在,而叙事的动心是情感,叙事的核心也是情感。对现实的把握来自于阅历,而诗意的流转来自于真情,这是《红楼梦》的余晖所光耀之处:将情感的意义放在最高处,将它作为时间的、地理的、人事的,一切存在的关联,而这样的观念与文学方法,此时此际,金风玉露,犹在《鹊桥仙》中回响。(苏七七)
来源: 北京青年报
对照式的故事有哪些3
作者:钱仓水(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我在不同年龄阶段读过,感受不一,先为其梗要叙述白蛇娘娘的故事吸引,后为其彻底的反封建压迫的思想感情打动。近二十多年来,我研究中华螃蟹文化,换了一个视角,又觉得鲁迅是一个技术娴熟的吃蟹行家,最近为追溯“蟹和尚”传说的来龙去脉,发现鲁迅更是一个在螃蟹话语上有继承开拓之功的文学大家。
蟹唐云/绘
“蟹和尚”的历史脉络
民间俗称的“蟹和尚”,实际上就是螃蟹胃袋里的胃磨。将螃蟹煮熟,揭开背壳,剥去黄膏,便是承接蟹口和食道的胃袋,圆锥状,外面包裹着灰白色的薄膜,里面常见食物残屑和泥沙。胃袋里有形态独特的骨质化咀嚼器,凭着肌肉的扩张收缩可以转动,把吞进的食物碾磨成细微颗粒,因为长在胃里,通称胃磨。把胃袋翻转,抖落污物,便见胃磨,整体黄褐色,头上一圈黑色,犹如削发后的圆顶,乍看,仿佛是一个披着袈裟打坐的和尚,这就是“蟹和尚”。
我先梳理一下中国人自宋至清认知“蟹和尚”的历史脉络。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蟹斗精上有孔,其中有子有泥,食之杀人。”这“蟹斗精上”,即蟹额区中间的蟹口,“孔”当是又短又直的食道,“其中有子有泥”,触及了食道末端的蟹胃和胃磨,“食之杀人”,它是不能吃的。明朝高濂《遵生八笺》:“《本草》云:蟹盖中膏内有脑骨,当去勿食,有毒。”历史上称《本草》的医药书籍甚多,此为何代何人所著,未详,谓“蟹盖中膏内有脑骨”,可以确定为胃磨,只是称作“脑骨”而已。
据我查考,最早把“脑骨”形象地叫作“蟹和尚”的,或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薛朝选,他在《异识资谐》里说:“蟹黄中有小骨如猴,俗呼蟹和尚。儿子擘酒蟹说,一僧兀坐胡床,余观之,果相似。近有上人作诗称为蟹壳仙者”(此书未见,转录自清孙之騄《晴川后蟹录》卷二“蟹仙”条)。这条文字,反映了时人观察到了蟹黄中骨质化的犹如“一僧兀坐胡床”的胃磨,称之为“蟹和尚”或“蟹壳仙”。
至清,屠绅在神魔小说《蟫史》第二十卷里说,交趾一贼,精气已铄,跃入江中,“乘海蟹空腹入之”,捞蟹人得而刳其腹,随手取出,“俨然盲僧”,点及“蟹和尚”由来。张南庄在滑稽小说《何典》里反复提到“蟹壳里仙人”,第六回中让其现身,一个“戴一顶缠头巾,生副吊蓬面孔,两只胡椒眼,一嘴仙人黄牙须”的道士,点及相貌。秦荣光在《上海县竹枝词》里说“无肠牵挂成和尚”,自注“蟹筐中有袋泥软壳,俗称蟹和尚”,点及处所。
以上种种说明,作为蟹腹中隐蔽而微小的“蟹和尚”,一方面已经写进笔记、医书、小说和诗歌,广为群众所知;一方面受到时代局限,所记又都显得简略、空疏、模糊、零星,没有留给人完整而清晰的印象。
全方位书面记录“蟹和尚”
1924年10月28日,鲁迅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从听说雷峰塔倒掉的消息写起,引出白蛇娘娘被法海和尚压在塔底的故事,再讲到玉皇大帝拿办法海,他逃到蟹壳里避祸,接着便是如此一段:
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这段文字浅显、优美、亲切,写法层层剥笋、步步推进、引人入胜,随着“煮”“取”“揭开”“吃”“露出”“切下,取出,翻转”一连串的动作,终于见到了“蟹和尚”。对照历史上“蟹和尚”的记录,明确地交代了它的位置,精准地说明了见到它的步骤,形象地勾勒了它的形态,从零星到完整,从模糊到清晰,从空疏到缜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鲁迅是全方位书面记录“蟹和尚”的第一人。
这段描叙文字的溢出意义,还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被后人仿效的操作模式。我就是其中一人。出于对“蟹和尚”,即躲在蟹壳里避难的“法海”的好奇,我按照鲁迅指示的程序和方法,曾经独自并为子女、为友人表演“捉拿法海和尚”。每次都兴趣盎然,反响热烈,当大家看到法海竟躲在如此封闭而窄小的胃袋里,与死鱼烂虾、浮萍水草为伴,也都从心底里喊出“活该”。
鲁迅为什么能够笔墨灵动、娓娓描叙呢?他是浙江绍兴人,“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自小爱吃会吃。之后,他关注过生物,学习过解剖,讲授过博物学,特别是从头到尾抄录过北宋傅肱《蟹谱》,发表过螃蟹脱壳的寓言式小品《螃蟹》。从这段文字可以推定,他早先一定对历史上所说“蟹和尚”产生过浓浓的兴趣,就在自己吃蟹的时候,刨根究底,仔细观察,经过知识储备,亲自摸索,于是才得心应手写出了这番朴实而精彩的话语。
“蟹和尚”与“法海禅师”
更可贵的,鲁迅又把“蟹和尚”引入了白蛇娘娘的故事里,成了这个故事冠冕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白蛇娘娘的故事,流传悠久,先见于笔记,后来写进了小说,搬演于舞台,说唱于书场,为我国四大传说之一,家喻户晓。
鲁迅小时候就听祖母讲了这个故事:
有个叫作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青蛇化作丫环,也跟着。
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漫金山”……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
雷峰塔是1924年9月25日倒塌的,当时报纸报道了这个消息后,人们议论纷纷。或说明其倒坍的原因,或回顾其建造的历史,更多的是对失去杭州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惋惜。当然,鲁迅也怦然心动,经过醖酿,博观约取,另辟蹊径,在一个多月后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他震聋发瞆地说:自我听了祖母讲述白娘娘故事,“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为什么呢?“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特别要说的,就在这篇杂文里,鲁迅把“蟹和尚”与“法海禅师”挂上了钩。“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不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对于这个挂钩,大家都毫不在意。其实,这是鲁迅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分体现,是前所未见的令人拍案称好的神来之笔。一方面使漂移了几百年的“蟹和尚”获得了一个人们熟知的身份,人格化了,一方面使人神共愤的“法海禅师”获得了一个永无出头之日的归宿,物质化了,相得益彰,融合为一。至此,白蛇娘娘的故事才算有了一个最终的圆满结局。
白蛇娘娘故事的圆满结局
鲁迅说,这个结局,“或者不在《义妖传》(按:清朝陈遇乾所著的讲述白蛇娘娘故事的弹词)中却是民间的传说罢”,诚然,不在《义妖传》中,可是,据我所知,亦不见之前所载的文字记录,故而推测,当是鲁迅萦绕心间已久的卓绝创作,退一步说,即使不是鲁迅自己的创作,那也是鲁迅把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在文学上作出的最早披露,无论哪种情况,鲁迅都是功不可没的,都是白蛇娘娘故事里最符合广大群众意愿的结局。
必须补充,自鲁迅首开记录说了“蟹和尚”就是躲在蟹壳里避难的“法海禅师”后,才陆续出现民间相关的后续故事:如说螃蟹背壳上为什么凹凸不平,那是青青见法海躲进去后用剑画的符,锁禁他;如说螃蟹本来是直着爬行的,自横行霸道的法海钻进去后只能横着爬动了;如说螃蟹嘴里为什么老吐白沫,那是法海在蟹腹里念经,妄想解脱……
常说鲁迅是有着特识卓见的文学大家,即以他的螃蟹话语而言,在《今春的两种感想》中讲了“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讲了“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这两个观点也闪耀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芒。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19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