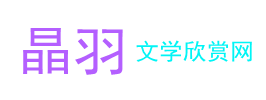清明节祭父母的散文
[散文]清明将至,十跪父母泪水已涟涟,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一江清水老刘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清明节祭父母的散文1
今天是2019年3月28日,再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细雨霏霏已好几天了,提前给这个清明节增添了一些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沉重的思念情怀。
清明节,是一个祭奠先人,缅怀远去的亲人的日子,是给远去的亲人扫墓的日子。因此,今天的心情就没有外面景色那么的“清明”了,而是更加地沉重和伤心,心中无时无刻地想念着亲人们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和点点滴滴。
我从2010年外出工作到今年,已是整整十个年头,每年的清明节都没能去坟上给远去的亲人们扫墓,只能是在路边上找个地方烧纸,借此表达对远去亲人们的思念。
今年的清明节前,由于疫情的原因,恐怕还是不能回去了,还是不能亲自到墓前给远去的亲人们扫墓和烧纸了;心情不由更加的沉重。看来只能等到4月21日,农历3月29日母亲三周年这天回去了。在母亲三周年祭日的这一天,亲戚们都会来,我们兄弟姐妹们也决定在这一天给父母的合葬立块碑。
人们都说只有过了三周年之后,去世的亲人才会真正的离开我们,三周年这一天亲戚们都会来纪念这一天,这一天也叫做“换孝”,之后就不会再悲痛和悲伤了。
是啊,你看,从此之后,兄弟姐妹们就再也不会为父母的事情聚集在一起了,就连再过春节时,对联都会换成红颜色的。每每想到这些,说实话心里依然不会好受,这一生一世与父母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吗?不!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分别,早晚我们还会再相聚的,为了我们的再相聚,父母只是先我们一步去探路了!父母子女之间这辈子相逢了,就结下生生世世的情,永永远远不会割断。
父亲于二OOO年的十月去世,至今已有二十个年头了;之前我也写过不少的文字来思念父亲,但无论千言万语,无论什么样的文字,始终都无法表达心中的思念,尤其是这些年来对父亲的思念更甚。母亲于2017年的农历3月29日去世,马上就到了三周年的祭日,去世的时候我不在身边,在得知噩耗的当时,那种撕心裂肺的悲痛和对母亲没有尽孝而深深自责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想起就会流泪。
父母啊,等到农历3月29日我再回去给你们立碑扫墓送纸钱,那个时候再回来和你们“相见”,再和你们“唠嗑”。
长跪父母坟前啊,泪水已涟涟。
一叩首啊,感谢父母带我来到这人世间;
二叩首啊,感谢父母含辛茹苦将我养育大;
三叩首啊,感谢父母教我读书识字教我做人的道理;
四叩首啊,不忘父母吃糠咽菜忍饥挨饿把粮留给儿女吃;
五叩首啊,不忘父母遭受冷眼求遍左邻右舍为儿女筹学费;
六叩首啊,不忘父母无怨无悔不辞辛劳养育子女照看孙子辈;
七叩首啊,父母离去从此阴阳相隔只能泪梦中相见痛断儿女心;
八叩首啊,父母离去儿女从此再也无法羊羔跪乳乌鸦反哺报答养育恩;
九叩首啊,愿父母天堂已相逢从此再无病和痛;
十叩首啊,祈盼来世再重逢,儿女定当床前尽孝再续父母子女情。
......
父母啊,千呼万唤再也不能相见,千跪万叩也无法表达对你们的思念!儿女们都很想念你们,你们可知道?
肝肠已寸断!父母啊,愿梦中常相见。
【2020年3月28日,农历3月5日于湖北谷城】
清明节祭父母的散文2
清明祭
铁韦
故乡的一草一树。一土一畦都会成为远方孤客的想念。
晋公子重耳怀揣乡土流亡列国。受尽磨难,在重耳饿得两眼发昏频临虚幻时,跟随他一路逃难的国士中,有一位叫介子推的,割股煮汤事主。重耳得势当上晋国国君后大赏有功之人。却唯独忘了介子推。介子推羞而不争,默不做声携老母离开。居于绵山。晋文公醍悟,遂派人召介为官。介未应文公。晋文公遂派人放火烧山以期逼出介子推。
介子推始终不出,背母焚于林中。文公悔恨悲伤,命定介子推焚身之日。国内不得生火,万民吃冷食。是为寒食节的由来。几千年生生不息,代代相承。历史换了一轮又一轮。而作为一种民族精髓得以传承下来。
中国有两个重要的节日。都是因气节而起。一个是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楚大夫屈原投江存义。一个是晋义士介子推坚守个人气节不惜焚身。慷慨事迹今天读起来依然悲壮激昂,捶胸长叹。我真的钦佩这些舍身求仁舍身存义的仁人志士。感觉这才是民族脊梁,民族真正应该发扬光大的精神。国之有士,民之福君之幸也。
也许爱读历史传记,古书古文的缘故,我或多或少也沾了一点古风。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权贵唱媚歌赞语。在厚黑学盛行的当下。也算是少有的另类吧。
我的家在洞庭湖平原。那是一方沃土。沟渠湖泊密匝。河流纵横。物产丰富。是殷殷实实的鱼米之乡。
记忆中的清明是在谷子下水时季。
少时家贫。衣叠补丁,食不裹腹。
大排面的祭祖是不可能的。肚子都填不饱,何来的钱米供奉祖先。过年过节筒简单单几个菜。点上香烛,烧三片钱纸,朝天地国亲牌位嗑了响头。母亲在旁喊几句祖宗保佑平安之类的就礼成了。
祭祀讲究仪式感。讲究心诚福至。祭拜时心里万万不可诽谤非议的。母亲叮嘱我们,亵渎了神灵,会遭报应。
祖宗保没保佑不知道。反正我就和那年代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迷迷糊糊地渡过了童年少年时光。也病过,溺水过。但终究是在半饥半饿中长大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叹生命的顽强。
每年清明节,抑或是其他重要的日子。村邻们都是要上街采买一番的。有时带了家里的鸡蛋或蔬菜到街上去卖变几个钱家用。那时家家都拮据,生活清苦。鸡下的蛋除重要节日重要人等能吃外。
其余的都是要攒下来卖钱的。一般是走七八里泥路到塞波咀老街去买点黄纸,蜡烛香什么的,都是便宜的,那年代物价平稳,挣钱虽难,但钱也值钱。几毛钱就可以买一大叠。母亲挎了竹蓝子和舅妈一起上街。先是沿家后面的湖走上三五里。而后拐去一条运河岸边小路。运河是早年开荒立垸的先辈挖拓的。十几米宽的样子。运河拐弯的地方有一座木架小桥通向老街。桥面用木板铺就。五尺来宽。有的钉子松了。不是很牢实,人走在上面。吱吱呀呀地响着。小孩子照例是要跟着去的。每回节日上街都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大小孩子们一路嬉戏,兴高采烈。大人们省吃俭用,总要从衣袋里拿出包着或红或紫的手帕布巾,拈出些角票分票银毫子,买几个法饼。有时还买点杏李桃子。慰劳孩子们。那时的果子真的好甜好香。也许是纯天然的缘故。没人做假,那年月是没有假货的。做假会遭到整个社会打击。反正年长后我再也没有吃出那种味道。
黄纸买回来后,我就提着去找我大堂哥。大堂哥名字
里有个学字,我就照当地的叫法。喊他学哥,学哥大我二十多岁,是大队上有名的木匠。忠厚一生,为人不玩套路。对我很好。学哥斜眼看了我拿的黄纸。笑眯眯地“又是么子具钻″。这是学哥发明的独特词汇,意思是套路事情。我觉得这个词汇很贴切生活。很是认可。
“具钻是借个凿子打下黄纸做冥钱″。
学哥转身在他的工具箱里找出了弧凿。打冥钱只能用弧凿,因为弧凿口是半圆的。打在黄纸上才可打出铜钱的样状。如果用方凿打出来的就不像铜钱了,先人收到用不了,会生气的,先人一生气,就不保佑后人了。后果是很严重的。到底有无阴间,众说纷纭。然而农村人是信的。耳濡目染,我也是信奉的。这就是宗教的力量。几千年的传承,刻进骨子里的信仰。它的效果有时比法律还管用。
总之在对待祖宗神仙这事上,无人敢作假,唬弄忽悠。
那时木工师傅每个大队都有几个。到了清明节前后。木工师傅的弧凿几乎就没闲停过。
我握住弧凿。右手拿了把小锤熟练的在黄纸上打钱。
冥钱打好后,母亲便用煮得烂熟稀糊的米饭将裁剪好的红绿纸用竹皮弓着糊个圆球。算是清明球。球是折成褶纹的。很深的皱。球是做什么用的。有老人说是灯笼。用以照亮先人来去的路。
“不是不准生火吗?还做什么灯笼″我连连问驳。
老人是有些道行“你懂么子。那是寒食节不生火,咯是清明″
“清明不就是寒食吗″我争辩。
“鬼扯腿,哪个讲的。寒食是寒食,清明是清明。清明在后,寒食在前两码事″老人读过私塾,是老一辈文化人。我虽有腹谤,却不敢放肆。后来我在书本上知道了这些。老人是对的。我知道我错了,我欠老人家一个道歉。然而我永远没有机会了。老人在一个冬天掉进了水沟里再也没有醒来,他去了另一个世界。
准备好了祭祀品,便是去坟墓地,先挂了球纸。点燃香火蜡烛。放挂十八响。十八个小鞭炮,一两毛钱,很是便宜。再虔诚跪下向先人磕头三回,整个仪式算是完了。
零三年在江西工作时,我才感到了清明节的隆重。所有的厂家是要放假祭祀先人的。做了如粽子一样的饭团,果子饭,加上菜肴放到坟冢边。向先人磕头致礼。
洞庭湖平原是没有这套礼节的。都是挂个红绿纸球,纸球下吊着一吊纸钱。据说在阴间的先人就会来取下那吊纸钱。
过去母亲在的时候,我因生计奔忙在外。每年的清明节都是由母亲挂球磕头的。
去年三月清明节前后,一场大病母亲再没有起来。从此祭祀挂球之事就由我自己来操理了。母亲和早逝的父亲合拱住到了一起。
母亲从祭祀者成了被祭祀的人。她和父亲就静静地安息在那里。旁边开满了油菜花。
母亲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永远。
清明节祭父母的散文3
乡情散文:壬寅清明祭
文:王世春
转眼又到清明了,“清明时节雨纷纷”,十余年来,每到这时,我的心情就如这风雨飘摇的隐晦天气,始终晴朗不起来。
还是给已故的父母双亲写点文字寄托哀思吧……
2011年3月14日(农历二月初十)夜里九点,父亲与世长辞了,走得是那样匆忙。
父亲是在老屋跟兄弟居住,那天下午六点下班后我顾不上回家,先到老屋去看他,他还嘱咐我打电话叫兄弟从街上买尿不湿来,叫住在后街的大妹给他煮点菜稀饭来,可能这就是我最后听到他说的话了。我刚回到家里做晚饭吃,饭没吃完,兄弟就打电话来,说父亲不行了,我急忙赶到老屋,只见他只能张嘴喘气,已经说不出话了。父亲似乎对自己有要离去的预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衣服都穿得很整齐,静静地躺在床上。到晚九点,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们五个子女都守在床前,可他临终前连句话也没留下。
父亲是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生人,我目睹了他从生病到去世的全过程,不过也就五个月时间。开始他是小便不畅,甚至解小便困难,我们把他送到医院诊断检查,说是前列腺问题,接着就是住院治疗,医生给他插上了导尿管,每天输液打针吃药,父亲性格有点古怪,象小孩子一样,既怕打针也怕吃药,得要劝着哄着他吃,若要他自己吃,他会悄悄把药丢了。没想到这前列腺住院一住就是两个多月,根本不见丝毫好转,我们五个子女轮流着排班,每家一晚在医院看护着他。他本来性格就有点古怪,人在病中更显得有些不耐烦,有时难免会发点小脾气,不管怎样,大家都很顺从他。
父亲从不喝酒,但烟瘾很大,住院后我们都控制着他,叫他尽量少抽或不抽,但有时看他实在熬不住,也只得给他点上一支。
不知怎样,父亲的前列腺始终治不好,人好象越拖越严重,在他住院的两个多月里,医院竟下了三次病危通知。第一次刚好碰上我们教研室到两汪乡送教下乡,我正给学生上中考作文指导课时电话来了,说是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我急忙把课讲完赶回来,到医院时,危险却解除了;第二次也是碰上我下乡,车刚要出城,电话又来了,我只得放弃下乡赶到医院,人又好些了。
谁也想不到,治了两个多月不见好转的前列腺在照了一次CT后,医生竟跟我和兄弟说是“肺癌”晚期,治不好了,我们说转院行吗?医生说那是徒劳,叫我们抬回去准备后事。我不大相信这个诊断,我记得2003年全国闹“非碘”时父亲也住过一次院,当时医生就说是“肺癌”晚期,但后来父亲竟还好好活了8年,不是“误诊”是什么?但这次医生又这么说,我就茫然了。
父亲抬回老屋后,医生既然说他是肺癌(但据说患肺癌的病人是很痛苦的,又从没见他叫痛),就权当作肺癌治吧。我从女婿那里抄了份治疗肺癌的中药方,据说是托人搞到的。有道是:病急乱投医。这药方有十多味草药,到中药房捡了药熬汤给父亲喝。父亲的求生欲望很强,总是问我这病还能好吗?我当然是安慰他说能好,我知道这是人在重病中对人生的依恋,但叫父亲喝草药汤却很难,一次只肯喝几小口,说太苦太难咽,好不容易才喝了几副。只见他好一阵差一阵,好的时候早餐能自己上街去吃米粉,吃了一碗米粉后还能吃一个油炸粑,精神也比较好,能在火盆边和我们烤火说话,我们认为他慢慢好起来了;但有时候状况又不好, 整天卧床不起。那段时间,好象父亲什么都想吃,我们尽量满足他,能买到的尽量给他买来,但他却吃得很少。
父亲和母亲一生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在他还没生病时,城里人总看到他和母亲早晚都在街上散步,人们都很羡慕这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能携手共度人生。现在父亲生病了,母亲的眼睛也快失明了,人也患了痴呆症,人们在街上见不到他们了。
我曾经把父母亲接到我居住的单位宿舍楼去住,但不知是因步梯楼层太高难爬,还是没熟人说话寂寞的原因,住了两个多月后,他们说什么都要搬回老屋去,我也只得由着他们。
这样的在老屋家里又拖了三个月,父亲还是走了。这位当年的“背爷生”、与奶奶相依为命、靠打草鞋为生的奶奶一手拉扯长大走出来的榕江国立师范学校的高才生、学生班长、学校演讲第一名获得者;解放初期的榕江栽麻乡中心校校长,后又经历了几年的工厂劳动改造和十多年的回乡劳动,平反后又当了十余年初中老师才退休,一生历尽坎坷的老人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86岁。
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我就留下了他的一根拐杖,一根他老年助步的拐杖,一根我人生旅途的拐杖。这根拐杖也将像伴随父亲一样伴随我的终身。
父亲去世后一年多一点,即2012年5月21日(农历五月初一),母亲也与世长辞。母亲的辞世是我最感伤的,因为她咽气的时候几个子女都在,唯独作为长子的我不在他身边。
那天上午,我随局里的教育督察组在栽麻小学督察,这是第一站,下午还要去中学,然后还有其他几个乡镇。上午工作结束在栽麻小学吃了中饭后准备午休一下,刚躺上床,家里的电话来了,说母亲不行了,叫我快赶回去。我跟带队领导说明了情况,急忙出门在公路上拦了一辆班车。往回赶的路上,不到30公里的行程,家里电话一直在催促我,说母亲真的不行了,快要咽气了,要我快去见最后一眼。电话里听到家人已经哭成一团,我当时的心情真不知道有多急,恨不能长了翅膀飞回去,但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等我赶到老屋家里,母亲已经走了,眼还睁着,我抱住母亲痛哭起来:“妈呀,你怎么就不等等我,让儿子看你最后一眼,儿子对不起您呀”。有道是:“自古忠孝难两全”。为了工作,我竟见不到母亲最后一眼,我一边哭着喊着,一边用手为母亲合上双眼。
母亲是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生人,享年82岁。父亲去世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母亲更显孤独,这时她已几近双目失明,而且患了老年痴呆症。开始时这些症状还不是这么严重,就是身体特别虚弱,把她送到医院住院,医生也检查不出是什么严重的病症,只是说人老了器官老化衰竭,也是常规性地输液打针吃药。我们也像照看父亲一样,五个子女轮流着排班,每家一晚在医院看护着她。她有时清醒明白,能认识人,能和我们说点话;有时又犯痴呆,连儿女都叫错了名字;我有个朋友来看她,送给她一百元钱,她拿着拿着却顺手扔在了床下。
这样的在医院也住了两个多月,母亲也不见好转,医生也说没有办法,只得把她抬回老屋家里。开始时,她还能自己洗脸、梳头、穿衣,吃饭,凭着熟悉摸到客厅里坐坐,眼睛也还能模糊视物。逢到周末,天气晴好,我就去老屋里搀扶她慢慢到街上去晒晒太阳,活动活动。但后来就不行了,母亲的状况越来越糟糕,这时她的眼睛已经完全失明,痴呆症也更严重了,经常说胡话,连儿女们都分不清楚了,有时还问父亲上街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
本来器官就老化衰竭,需要很好的营养补充和调养,但母亲的饮食不行,什么也吃不下,只能喝点稀饭和豆腐脑,沾到点肉沫就吐出来。到最后的一个月,母亲的状况更糟糕了,整天就是昏睡,连大小便也失禁在床上,也很难为了媳妇和女儿们经常给她换洗擦身。我平时上班下乡太忙,尽孝心不够,一有空就往老屋跑,每逢周末休息一大早就给她买去稀饭或豆腐脑、甜酒粑(豆腐脑和甜酒粑是她平时爱吃的),一勺一勺地喂她吃,只盼她能多坚持一段时间,可是母亲还是走了。
母亲一生勤劳、俭朴、善良,从小就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是个典型的乡下农村妇女。常言道:儿多母苦,母亲一生生育了七个儿女(其中有两个在大饥荒的年代里夭折了),那种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了。她的一生就知道劳动和养育儿女,直到父亲退休,儿女都成家立业后,才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我是长子,几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生起,就一直陪着母亲共同度过那些艰难的岁月,见证了母亲一生的勤劳和艰辛。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直都是很疼爱我的,特别是在那饥饿的年代,宁愿自己不吃或少吃,都要省给我吃。我出来工作后,弟弟妹妹们都还小,母亲仍然在艰辛劳作,几十年来我每个月从不间断给母亲一点零花钱,而母亲每次都是很客气地谦让一番,她哪里知道,儿子虽是工薪阶层,纵然有座金山,也换不来她伟大的母爱啊。
母亲走了,她的坟茔就在父亲旁边,但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依旧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携手前行。
作者简介:王世春,苗族,1952年生,贵州省榕江县人,退休教师,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业余文学创作,有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在省内外各级公开刊物和网络平台发表,出版过纪实文学专集《人生驿站》和散文集《向晚吟》。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若侵权联系删除。欢迎文友原创作品投稿,投稿邮箱609618366@qq.com,本号收录乡土、乡情、乡愁类稿件。随稿请附作者名,带图片最好,请标注是否原创。乡土文学公众号已开通,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xiangchouwenxue,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