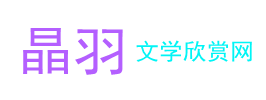梁实秋有关读书的文章
梁实秋:流连而不忍离去,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经济观察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梁实秋有关读书的文章1
欧阳霞/文
当梁实秋在台北的家中接过女儿转辗从青岛带去的一瓶海沙时,已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了。晚年的梁实秋每每凝望海沙的时候,那些曾经呼啸在他年轻血管的、曾经流淌在他激情笔端的、曾经让他哭、让他笑、让他歌的往昔生活一瞬间从心底涌起……
1930年夏天,梁实秋通过闻一多结识了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杨振声邀请梁实秋和闻一多赴青岛任教,那一刻伸向梁实秋的橄榄枝如同一道生命的曙光般意义非凡。那时延续了三年的文坛论战令梁实秋精疲力竭,他也早已厌倦了上海令人窒息的喧嚣和刻薄。1927年1月,梁实秋在《复旦旬刊》创刊号发表文章《卢梭论女子教育》,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关于男女平等教育、注重女子经济独立等观点进行了批评。梁实秋认为男女在“自然”上便是有差别的、“不平等”的,所以即使主张女子经济独立,即使女子比男子做得还好,“她已失去了她的女子特性”。此文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最先惹恼的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一位署名“振球”的女生写文章质问梁实秋:“我们不晓得梁先生的居心究竟怎样?难道要我们女子永处于被男子玩弄、压迫的‘特性’地位,男子可以做的事,我们永远不好去做吗?”另一位署名“研新”的学生则写文章讽刺梁实秋,大意是:梁老师你是不是误解了卢梭的男女平等观念?你所谓的男女有别,不是瞎胡扯吗?
出生于书香门第、求学于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思想理念深受其老师白璧德影响的梁实秋,一时间承受不了学生的批评,他立刻致信《复旦旬刊》编辑部称:“吾人撰述学术文字,首宜屏除意气,在文字方面尤当力求点检,粗俗鄙陋之词句,与讥讪揶揄之语调,皆应避免,因讨论学术之文字,体例固应如此。近人为文,常趋于轻浮一派,且喜牵涉个人,非所以讨论学术之道也。秋之专攻,在于批评,故读他人评我之文最为欣幸,惟批评之态度必须求其严谨耳。”显然,这封信更多的是个人权威受到学生挑战后的情绪释放,回避了对问题的回答和讨论。
由此可见,梁实秋那时完全没有论战的准备,他做梦都没想到一个强大到他无法抵御的论敌正在向他走来。1927年10月,鲁迅应陈望道邀请到复旦大学演讲。读到《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后,树人兄眉头一紧,心生警觉,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岂不是要开新文化运动的倒车吗?于是,鲁迅在《语丝》周刊上连续发表《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拟豫言》等文章驳斥梁实秋,刀刀见血,飞花摘叶皆可伤人。
随后,鲁迅的好友郁达夫也在《北新》半月刊发表《卢梭传》《翻译说明就算答辩》等文章,接茬复旦学生,劝告梁实秋“多读几年卢梭的书再来批评他罢”。当时留学归来的梁实秋只有24岁,虽因写了几首新诗被称为“豹隐诗人”,但与已是文坛巨擘的鲁迅论战,简直就是以卵击石。但年轻气盛的梁实秋还是奋起应战,不断写论文坚持将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和文学观,否认文学有阶级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
一石激起千层浪,梁实秋遭到左翼作家群体的围攻。于是,这场文坛论战如无法扑救的山火般熊熊燃烧,绵延不绝,论战主题扩展到“文学的阶级论与人性论”、“第三种人”、翻译理念、文艺政策等话题,也逐渐由学术争论发展到意气之争。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中影射鲁迅等左翼作家“通共”、“通俄”。是可忍孰不可忍!鲁迅撸起袖子写下了后来收入中学教材的名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资本家的乏走狗”这顶帽子,梁实秋一辈子都没有摘掉。而这场论战一直延续到鲁迅去世,至死方休。
1930年,杨振声为新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招揽人才,梁实秋和闻一多携手奔赴青岛,逃离了沪上的纷争。
青岛红瓦绿树,三面临海,“山坡起伏绿树葱茏之间,红绿掩映”,梁实秋纷乱的心绪渐渐被安抚,他绝意于文坛硝烟而潜心读书、教书和写作。梁实秋在青岛鱼山路7号(现为鱼山路33号)租下了一栋小楼,任教于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担任《英国文学史》《文艺批评》等课程的教学。
在课堂上,他声情并茂地讲授西洋戏剧的代表作和发展史;讲授莎士比亚的生平和剧作;讲授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梁实秋对自己的教学自信满满,他对学生说:“我讲课,只要听之者不是下愚,不是根本不听,总能得其梗概,略具颖悟,稍加钻研,必可臻于深到。”而学生也总是将敬佩的目光投向梁老师。
那时候,梁实秋天天步行到校,身着中式裤褂和飘逸长袍,行走于崎岖小路,风神潇洒,旁若无人。除了教学,梁实秋更多的时间用在读书、写作和翻译上。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书目中包括《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二十一史》。
梁实秋还兼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学校初建,藏书不多。为了学校的图书建设,本不想再回上海的梁实秋还是赴沪釆购图书,并四处搜罗各类书籍。当梁实秋听说崂山太清宫藏有一部珍貴的《道藏》时,立刻求助教育部帮忙将《道藏》移至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但未能如愿。躲在青岛的梁实秋还是躲不过鲁迅的利剑,鲁迅写文章指责梁实秋,大意是:你凭什么利用职务之便,在大学的图书馆下架俺的书?梁实秋没有应对。直到1964年,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提及这段旧事, 说:“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
梁实秋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对家庭生活更是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到青岛的第一天,他就认定青岛旖旎的风光和凉爽的气候宜于定居。他在《忆青岛》中说:“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北平从繁华而破落,从高雅而庸俗、而恶劣,几经沧桑,早已无复旧观。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青岛的干净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北平不能比的。
梁实秋租住的房子有宽敞的院子,据资料记载院子里栽种了六棵樱花树、两棵苹果树和四棵海棠树。但我估计并不会有樱花树,他在《忆青岛》中说:“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和我们有血海深仇,花树无辜,但是我不能不连带着对它有几分憎恶!”。我想大概也不会有海棠树吧,梁实秋的名著《雅舍小品》,写于1940年抗战中的重庆,其中《病后杂谈》篇开头写道:“鲁迅曾幻想到吐半口血扶两个丫环到阶前看秋海棠,以为那是雅事。”
梁实秋常常自己动手在院内种花植树,一座寻常屋舍,在他的手中变得性灵情致,每当看着孩子们在繁花如簇的院子里嬉戏打闹时,他深切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贤良的妻子、乖巧的儿女、美丽的青岛,他多么想就这样波澜不惊地生活到老。那时候,在他的晚年掀起爱情巨浪,让年逾古稀的梁实秋秒变情窦初开少年的韩菁清女士还未出生。
“我们虽然僦居穷巷,住在里面却是很幸福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自己的家更舒适。”在青岛这处幽雅的小院里梁实秋度过了一生中家庭生活最幸福的四年。也正是在这里,梁实秋开始了最为后人所钦仰也是规模最为浩大的工程——《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
1930年底,在胡适提议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将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列上工作日程。胡适选定闻一多、梁实秋、陈西滢、叶公超和徐志摩为翻译委员,计划五至十年完成。梁实秋始终毫无保留地投入翻译工作,他“广泛收集参考资料,发掘未经删节的版本,经过反复斟酌后选择了散文体翻译。”“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抓着功夫翻译”。而其他四人,出于种种原因,并未投入这项工作。
翻译是很寂寞的事,尤其是面对莎士比亚多达三十七种的戏剧,外加三部诗集,梁实秋为此“穷年累月,兀兀不休”。这项巨大的翻译工作在他离开青岛以后间断了,直到1967年,梁译《莎士比亚全集》才最终完成并出版,前后花费了近四十年。胡适一直关注着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工作,他对梁实秋说,等全集译成之时他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庆祝酒会。可是,胡适先生没有等到《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就去世了。
在青岛的后两年,梁实秋专心治学,也渐渐形成了保守温和的人生态度。他不走极端,不冒风险,但也坚守原则,不随波逐流。青岛山明水秀,但“没有文化”,也没有适当的娱乐,天长日久,梁实秋感到日子有些乏味了。本就好酒的梁实秋于是呼朋聚饮,推杯换盏,猜拳行令,经常是薄暮入席,夜深始散。曾应邀到青岛演讲的胡适说:“青大诸友多感寂寞,无事可消遣,便多喝酒。连日在顺兴楼,他们都喝很多的酒。”梁实秋说:“送往迎来以及各种应酬,亦无不出于饮食征逐的方式”。
青岛也绝非世外桃源,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这一切都不能不影响到梁实秋的宴席,也击碎了他娴静优雅的名士梦。
国立青岛大学爆发学潮,校长杨振声辞职。1932年7月,教育部决定解散国立青岛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杨振声、闻一多相继离开青岛,梁实秋却留下来继续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教。但酒席散了,朋友走了,让梁实秋“流连不忍去”的青岛也越来越空洞起来。正在梁实秋彷徨无着的时候,从北京传来了胡适先生热切的召唤,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胡适写道:“我希望你和朱光潜君一班兼通中西文学的人能在北大养成一个健全的文学中心,我感觉近年全国尚无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文科,殊难怪文艺思想之幼稚零乱。此时宜集中人才,汇于一处,四五年至十年之后,应该可以换点气象。”胡适又说:“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大来吧!”。尽管当时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先生再三挽留,但梁实秋还是于1934年7月离开了青岛。
梁实秋有关读书的文章2
作者:梁实秋 诵读:王卉
人的天性大致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习惯方面各有不同。习惯是慢慢养成的,在幼小的时候最容易养成,一旦养成,要想改变过来还不很容易。
例如,清晨早起是一个好习惯,这也要从小时候养成。很多人从小就贪睡懒觉,一遇假日便要睡到日上三竿还高卧不起,平时也是不肯早起,往往蓬头垢面地就往学校跑,结果还是迟到,这样的人长大之后也常是不知振作,多半是不能有什么成就的。祖逖闻鸡起舞,那才是志士奋励的榜样。
我们中国人最重礼,因为礼是行为的轨范(此处原文为“轨范”,无笔误),礼要从家庭里做起。姑举一例:为子弟者“出必告,反必面”,这一点点对长辈最起码的礼,我们是否已经每日做到了呢?
我看见有些孩子早晨起来对父母视若无睹,晚上回到家如入无人之境,遇到长辈常常横眉冷目,不屑搭讪。这样的跋扈乖戾之气如果不早早纠正过来,将来长大到社会服务,必将处处引起摩擦不受欢迎。我们不仅对长辈要恭敬有礼,对任何人都应维持相当的礼貌。
大声讲话,扰及他人的宁静,是一种不好的习惯。我们试着自我检讨一番,在别人读书、工作的时候是否有过喧哗的行为?
我们要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维持公共的秩序,顾虑他人的利益,不可放纵自己,在公共场所人多的地方,要知道依次排队,不可争先恐后地乱挤。
时间即是生命。我们的生命一分一秒地在消耗着,我们平常不大觉得,细想起来实在值得警惕。我们每天有许多零碎时间于不知不觉中浪费掉了。我们若能养成一种利用闲暇的习惯,一遇空闲,无论多么短暂,都利用之做一点儿有益身心之事,则积少成多,终必有成。
常听人讲“消遣”二字,这最是要不得,好像是时间太多无法打发的样子。其实人生短促极了,哪里会有多余的时间待人“消遣”?陆放翁有诗云:“待饭未来还读书。”我知道有人就经常利用这“待饭未来”的时间读了不少书。
古人所谓“三上之功”,枕上、马上、厕上,虽不足为训,但其用意值得借鉴,都是在劝人不要浪费光阴。
吃苦耐劳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标志。古圣先贤总是教训我们要能过得俭朴的生活,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就是形容生活状态之极端的刻苦;所谓“嚼得菜根”,就是表示一个有志的人得能耐得清寒。
恶衣恶食,不足为耻,丰衣足食,不足为荣,这在个人修养上是应有的认识。
罗马帝国盛时的一位皇帝——Marcus Aurelius,他从小就摒绝一切享受,从来不参观当时风靡全国的赛车、比武之类的娱乐,他终其一生成为一位严肃的苦修派的哲学家,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以上不过是偶然拈来,好的习惯千头万绪,“勿以善小而不为”。习惯养成之后,便毫无勉强,临事心平气和,顺理成章。
充满良好习惯的生活,才是合于“自然”的生活。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微信关注:ihxdsb,报料QQ:3386405712】
梁实秋有关读书的文章3
从前有一个朋友说,世界上的好书,他已经读尽,似乎再没有什么好书可看了。当时许多别的朋友不以为然,而较长一些的朋友就更以为狂妄。现在想想,却也有些道理。
世界上的好书本来不多,除非爱书成癖的人(那就像抽鸦片抽上瘾一样的),真正心悦诚服地手不释卷,实在有些稀奇。还有一件最令人气短的事,就是许多最伟大的作家往往没有什么凭借,但却做了后来二三流的人的精神上的财源了。柏拉图、孔子、屈原,他们一点一滴,都是人类的至宝,可是要问他们从谁学来的,或者读什么人的书而成就如此,恐怕就是最善于说谎的考据家也束手无策。这事有点怪!难道真正伟大的作家,读书不读书没有什么关系么?读好书或读坏书也没有什么影响么?
叔本华曾经说好读书的人就好像惯于坐车的人,久而久之,就不能在思想上迈步了。这真唤醒人的迷梦不小!小说家瓦塞曼竟又说过这样的话,认为倘若为了要鼓起创作的勇气,只有读二流的作品。因为在读二流的作品的时候,他可以觉得只要自己一动手就准强,倘读第一流的作品却往往叫人减却了下笔的胆量。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部分的真理。
也许世界上天生有种人是作家,有种人是读者。这就像天生有种人是演员,有种人是观众;有种人是名厨,有种人却是所谓“老饕”。演员是不是十分热心看别人的戏,名厨是不是爱尝别人的菜,我也许不能十分确切地肯定,但我见过一些作家,却确乎不大爱看别人的作品。如果是同时代的人,更如果是和自己的名气不相上下的人,大概尤其不愿意寓目。
我见过一个名小说家,他的桌上空空如也,架上仅有的几本书是他自己的新著,以及自己所编过的期刊。我也曾见过一个名诗人(新诗人),他的惟一读物是《唐诗三百首》,而且在他也尽有多余之感了。这也不一定只是由于高傲,如果分析起来,也许是比高傲还复杂的一种心理。照我想,也许是真像厨子(哪怕是名厨),天天看见油锅油勺,就腻了。除非自己逼不得已而下厨房,大概再不愿意去接触这些家伙,甚而不愿意见一些使他可以联想到这些家伙的物事。职业的辛酸,也有时是外人不晓得的。唐代的阎立本不是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再做画师么?以教书为生活的人,也往往看见别人在声嘶力竭地讲授,就会想到自己,于是觉得“惨不忍闻”。做文章更是一桩呕心血的事,成功失败都要有一番产痛,大概因此之故不忍读他人的作品了。
书
从前的人喜欢夸耀门第,纵不必家世贵显,至少要是书香人家才能算是相当的门望。书而日香,盖亦有说。从前的书,所用纸张不外毛边连史之类,加上松烟油墨,天长日久密不通风自然生出一股气味,似沉檀非沉檀,更不是桂馥兰薰,并不沁人脾胃,亦不特别触鼻,无以名之,名之日书香。书斋门窗紧闭,乍一进去,书香特别浓,以后也就不大觉得。现代的西装书,纸墨不同,好像有一股煤油味,不好说是书香了。
不管香不香,开卷总是有益。所以世界上有那么多有书癖的人,读书种子是不会断绝的。买书就是一乐事,旧日北平琉璃厂隆福寺街的书肆最是诱人,你迈进门去向柜台上的伙计点点头便直趋后堂,掌柜的出门迎客,分宾主落座,慢慢地谈生意。不要小觑那位书贾,关于目录版本之学他可能比你精。搜访图书的任务,他代你负担,只要他摸清楚了你的路数,一有所获立刻专人把样函送到府上,合意留下翻看,不合意他拿走,和和气气。书价么,过节再说。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个读书人很难不染上“书淫”的毛病,等到了四面卷轴盈满,连坐的地方都不容易匀让出来,那时候便可以顾盼自雄,酸溜溜地自叹“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现代我们买书比较方便,但搜访的乐趣,搜访而偶有所获的快感,都相当地减少了。挤在书肆里浏览图书,本来应该是像牛吃嫩草,不慌不忙的,可是若有店伙眼睛紧盯着你,生怕你是一名雅贼,你也就不会怎样的从容,还是早些离开这是非之地好些。更有些书不裁毛边,干脆拒绝翻阅。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日:‘我晒书。’”(见《世说新语》)郝先生满腹诗书,晒书和日光浴不妨同时举行。恐怕那时的书在数量上也比较少,可以装进肚里去。司马温公也很爱惜书的,他告诫儿子说:“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净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晒其脑。所以年月虽深,从不损动。”书脑即书的装订之处,翻页之处则日书口。司马温公看书也有考究,他说:“至于启卷,必先向案洁净,借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曾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污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随覆以次指面,捻而夹过,故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见《宋稗类钞》)我们如今的图书不这样名贵,并且装订技术进步,不像宋朝的“蝴蝶装”那样的娇嫩,但是读书人通常还是爱惜他的书,新书到手先裹上一个包皮,要晒,要揩,要保管。我也看见过名副其实的收藏家,爱书爱到根本不去读它的程度,中国书则锦函牙签,外国书则皮面金字,庋置柜橱,满室琳琅,书变成了陈设、古董。
有人说:“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有人分得更细:“借书一痴,惜书二痴,索书三痴,还书四痴。”大概都是有感于书有借无还的。书也应该深藏若虚,不可慢藏诲盗。最可恼的是全书一套借去一本,久假不归,全书成了残本。明《五杂俎》,记载一位“虞参政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小木为徇,夜则去之。榜其门日:‘楼不延客,书不借人。’”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惜一般人难得有此设备。
我们国内某一处的人士最好赌博,所以讳言书,因为书与输同音,读书曰读胜。基于同一理由,许多地方的赌桌旁边忌人在身后读书。人生如博弈,全副精神去应付,还未必能操胜算。如要沾染上书癖,势必呆头呆脑,变成书呆,这样的人在人生的战场之上怎能不大败亏输?所以我们要钻书窟,也还要从书窟里钻出来。朱晦庵有句:“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去寻春。”是见道语,也是老实话。
旧书铺
我所看见的在中国号称“大”的图书馆,有的还不如纽约下城十四街的旧书铺。纽约的旧书铺是极引诱人的一种去处,假如我现在想再到纽约去,旧书铺是我所要首先去流连的地方。
有钱的人大半不买书,买书的人大半没有多少钱。旧书铺里可以用最低的价钱买到最好的书。我用三块五角钱买到一部Jewett译的《柏拉图全集》,用一块钱买到第三版的《亚里士多德之诗与艺术的学说》就是最著名的那个Butcher的译本——这是我买便宜书之最高的纪录。
罗斯丹的戏剧全集,英文译本,有两大厚本,定价想来是不便宜,有一次我陪着一位朋友去逛旧书铺,在一家看到全集的第一册,在另一家又看到全集的第二册,我们便不动声色地用五角钱买了第一册,又用五角钱买了第二册。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在三家书铺又拼凑起一部《品内罗戏剧全集》。后来我们又想如法炮制拼凑一部《易卜生全集》,无奈工作太伟大了,没有能成功。
别以为买旧书是容易事。第一,你这两条腿就受不了,串过十几家书铺以后,至少也要三四个钟头,则两腿谋革命矣。饿了的时候,十四街有的是卖“热狗”的,腊肠似的鲜红的一条肠子夹在两片面包里,再涂上一些芥末,颇有异味。再看看你两只手,可不得了,至少有一分多厚的灰尘。然后你左手挟着一包,右手提着一包,在地底电车里东冲西撞地踉跄而归。书铺老板比买书的人精明。什么样的书有什么样的行市,你不用想骗他。并且买书的时候还要仔细,有时候买到家来便可发现版次的不对,或竟脱落了几十页。遇到合意的书不能立刻就买,因为顶痛心的事无过于买妥之后走到别家价钱还要便宜;也不能不立刻就买,因为才一回头的工夫,手长的就许先抢去了。这里面颇有一番心机。
在中国买英文书,价钱太贵还在其次,简直的就买不到。因此我时常的忆起纽约的旧书铺。
转自MOOC
作者:梁实秋 (1903一1987)原名梁治华,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代表作《莎士比亚全集》(译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