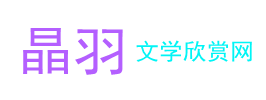儿时杀猪说说(杀猪的经典说说)
关于杀猪宴的回忆,满满的幸福感,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本草纲目谜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儿时杀猪说说(杀猪的经典说说)1
我是上世纪80年代生人,我的家在东北。对于小时侯的杀猪菜有着满满的回忆,每逢过年杀猪就像是一场盛大的节日,令人兴奋不已。
记得在我小时候,在老家农村,几乎每家都有杀年猪的习惯,那时候每家每户家里都会有一个猪圈,春天的时候会抓一个或几个猪羔子来养,养到年底然后杀掉。小门小户的家庭即便杀猪,也是自己留一小部分猪肉,然后大部分都肉用来拿到集市上或者是在村子里卖掉,那时候养猪的最主要目的是赚钱用来过年。
那时候农村几乎没有冰箱,所以自己家留一部分猪肉用来过年,猪肉的贮存方式就是装在袋子里或者缸里自然冷冻,再有一部分用盐淹渍起来,这样能贮存时间长一些,然后用于第二年招待客人用。
每年杀猪的时候,都像是一场盛宴。杀猪就像过年一样,杀猪也是快过年的一个信号,杀猪的日子,也都是往往选择在临近春节,因为家里杀猪后,每天都可以吃到肉了,而且能吃到过年后。因此,无论对于大人还是对于小孩来说,杀猪都是特别开心的事情。
记得每年家里杀猪的时候,那一天都是会特别早的醒来。然后家人会把杀猪的师傅请到家里吃饭,吃完饭后就开始抓猪,然后杀猪师傅开始杀猪,杀猪的时候家里会请好几个人打下手。猪被杀死后,开始用开水烫猪毛,然后开始庖解猪的身体,开始把整头猪卸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肉。然后杀猪师傅还会整理猪的下水,家人以及打下手的人们会开始搅拌猪血,灌血肠。准备烀肉。
这一天,往往会把家里的家族、亲戚,朋友,左右好邻居等各种各样的客人请到家里吃杀猪菜,亲人们会有说有笑的做杀猪宴,人们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杀猪结束后,第一个环节就是烀猪肉,乎猪肉的香味会飘满半个村落,那是多么难当的诱惑。香气飘飘的猪肉,是农村人幸福喜悦的最好表达。
把猪肉烀熟之后,然后开始炖酸菜,酸菜里放满五花肉和血肠,然后会蒸一大盆猪血,妈妈和家里帮忙的女人们还会用下水以及猪肉做几道香喷喷的菜,杀猪菜那简直是美味极了。
大碗的猪肉、大碗的猪血摆在不加修饰的桌子上,然后亲朋好友们便开始围坐在一起吃肉,喝酒,辛辛苦苦忙了一大年的人们,也许就是等着这一顿美美的杀猪宴,太幸福和美味了,那种感觉是真的溢于言表。
小孩们也是特别开心,等大人把猪肉烀熟的时候,便开始先尝个鲜。大人们往往把拆好的瘦肉再准备一些蒜泥,小孩们便先吃起来。吃完之后幸福的满街跑,快过年了,真是开心呐。
小时候每逢家里杀猪这一天,都是无比快乐的!因为这一天,不仅仅是吃香喷喷的肉。重要的是那种热闹喜庆气氛会让你感到所有的事情都是幸福。而且,这种幸福会一直延续到过年,快到过年的时候,农村会迎来杀猪的高峰期,吃完自己家的猪肉,还会随着爸爸妈妈去别人家吃。比如姥姥家,舅舅家,叔叔家,姑姑家,朋友家,非常朴素的农村生活却有着崇尚礼尚往来的良好传统。今天到我家来吃肉,明天也许又要到你家去做客,这种你来我往,往往会使唤幸福感加倍和爆棚。
大碗茶,大碗酒,大碗饭,大碗肉。穿的是破布粗衣,乘坐的是不用耗油的交通工具,嘴上一笑,或许还能露出一排大黄牙,幸福的农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也许都是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农村饭菜,没有什么花哨,但是却幸福感满满。
随着时间的流淌,岁月的流逝,时代的进步。农村每年腊月杀猪这一风俗也渐渐的被改变了。现在农村生活条件好了,反倒不去养猪了。家里有冰箱,市场的物质又那么丰富,平时就能吃到猪肉,也无需靠养猪来贴补家用。所以渐渐地农村养猪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种过年杀猪的喜悦和兴奋也慢慢的消失和淡化了。
慢慢的杀猪宴成了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一道永远不能抹杀的回忆。现在许多城里人也去农村去寻找吃杀猪菜的感觉。但是现在农村能够过年杀猪的,真是凤毛麟角,越来越少见了。
即便有杀猪的,也是现囤来的猪。但是现在人还是那个人,但是猪却不是过去的那个猪了。过去的那个猪,善良淳朴,一味的吃粮食长大。现在的这个猪,吃着各种的饲料精华,被整个世界催着长大,因此,再也无法找到从前那个朴实无华的猪了。所以人们即使能吃到杀猪宴,也不像是过去那种朴实无华的杀猪宴了。
所以对我这个年代的人来说,或者是60、70年代人来说。杀猪宴也慢慢的变成一种奢侈的回忆。再想吃到小时候那种纯朴的杀猪菜,也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了。
但是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世界无论怎样改变。杀猪菜留给我们的满满的回忆,满满的幸福感依然还是永远地珍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图片来自网络)
儿时杀猪说说(杀猪的经典说说)2
有人问我,陈大爷不见了,你报警之后咋不接着往下说?其实我是觉着真没啥好说的。胡支书报完警,当天晚上镇上派出所来人做了笔录。隔两天又来了几辆外地牌照的车和一辆军车,把石夫人顶上给封起来了,全村人都被叫去问话。除了山顶不让村民去了之外,生活没有任何变化。至于到底发生了啥,陈大爷究竟去没去石夫人,是不是像小涛说的被UFO劫走了,没人知道。你们可别看我嘴上说的是云淡风轻,在我心里边这事是个坎。到底陈大爷发生了啥事,到底有没有个透明三角形停在半空,我比谁都想弄明白。
这回我主要想说说杀猪的事情。这行我干了也十多年了,熟门熟路。抓着猪四脚绑好仰放在台子上把猪头挂出来,摸着脖子连身体那地方,用力一刀捅进去转个半圈,然后拔出来等血放干。刀要长,一刀进去够不着捅不破心脏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干熟练了之后也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事儿,跟平常单位里上班摸鱼看报纸其实没啥本质的区别。除了一件事情,准确的来说,是一头猪。让我记忆犹新,如鲠在喉,不说出来不痛快。
三年前村里不给养猪了,也不让农户自己杀。镇上有个屠宰场,农户自家养的最后一批猪都一起运过去杀了。这时胡广来,我们都叫他“胡来”,包下了屠宰场,又在屠宰场附近靠山这块圈了几百亩的一大块地,办起了养猪场。胡来是镇上唯一一个把养猪的八本资质证书全办下的人,这钱只能还得他赚。
说起胡来,年龄比我小点儿,村支书儿子。去外国留过学待过几年,回来吃的开,人面广。他办养猪场我是出了分力的,选地建猪舍买设备饲料我都提了意见,毕竟这活我熟。他也没亏待我,让我把屠宰资格证考了,去他那上班。我说资格证我有,上班就算了。村里卖肉习惯了,坐厂里办公室不舒心,再说我去他那上班了,全村人就没地儿买肉了。于是他就给我配了辆金杯车,说村里人喜欢吃农家自养的猪。他有一批两头乌,是准备在山里放养的。到时我就去镇上连杀带宰,把肉运回村子里卖,价格算我便宜,当他的分销商。我一听这活计好,赶紧答应了。
有人说我太啰嗦,前面铺垫太长,就是不说发生了啥。凡事都讲究个前因后果,不把起因给介绍了,这原本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来龙去脉的事,到了听的人那岂不更是一头雾水了?也有的人说我说的不够详细,很多地方一笔带过。怎么,要不从三年前的一天我愁眉苦脸躺在床上琢磨小涛的学费咋办的时候说起:
我正愁着呢,电话响了。我没接,心里只想着不能杀猪了以后该怎么找钱。电话又响了一遍,我被烦得慌便接了起来,粗声粗气问:“谁啊?”电话那头传来一把浑厚低沉的男声,不带任何口音的说:“富贵哥,是我,胡来。你能不能到镇上来一趟?我想在屠宰场后边再建个养猪场,我爸说这事儿得跟你商量商量。”
要是这样说,光建猪场的事我都能说上个十天八夜的,我自己都觉得累。养猪那八本证书怎么批,猪场怎么建,设备怎么买,饲料怎么选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猪场建好之后,我又去了镇上一趟。一来是参观参观,二来是拿上那辆已经改装了货架的金杯车。
那天天气非常好,一片透明的蓝天上点缀着几块稀碎的云。空气纯净,视野开阔。我远远就望见胡来穿了条迷彩工装裤,上身套了件深蓝色牛仔,带了几个人,在养猪场门口等。边上是白围墙,看不出围了多大一圈,只知道很大。中间一个大铁门,门上面做了个拱桥型的灯箱,五个大字写着广来养猪厂。胡来见我到了,扔掉手里的烟头,招呼人去把我脚踏车停了,便亲热的搂着我的肩,带我进去参观。
进了养猪场大门,在值班室里登了记,胡来领着我进到一个更衣消毒室。等我套上一件连体工作服出来,门口就是一条新修的大约有三个车道宽的水泥路。我对胡来说:“胡来,你这卫生标准是跟国际接轨了吧?”
胡来咧开了嘴,“那必须,要做就得做最好的。况且你说了,卫生标准越高,得病率越低,产仔存活率也越高啊。”他指着水泥路右手边说:“这边全是高密度猪舍。按你的建议,公母猪、产仔保育、育肥都分开了。类型我选了全封闭式,除了贵没别的毛病。猪也听你的进了批英国pic的五元猪,目前母猪存量有五百头。”
看着这一片猪舍,我心里合计这投资应该要在两千万以上了,边感叹边嘴上不忘对他的员工吹嘘,“英国pic好啊,省饲料,发育快,5个月就能到200多斤。现在猪肉贵,尽量往大了养,越大饲料转换率越高。猪舍跟猪舍中间最好再种点果树、绿植啥的,平时净化空气,夏天可以遮阳。”
胡来让人把种树这事记下,便带着点神秘兮兮的兴奋拉着我的手,往左边一条道走去,说:“来,给你看好东西。”
我一看道路尽头那山坡底下一排大平房就知道,这肯定就是放养的猪舍了。我们穿过围栏进到里面,我却发现设施完备,地方却空旷的很——空旷到里面一只猪都没有。
胡来看出我眼中的疑问,哈哈大笑,向身后招招手,马上有员工递上一台笔记本电脑。胡来打开指着屏幕上的那些凌乱的红点问我,“你猜猜,这是啥?”
“不是吧!胡来,你在每头猪身上都装了定位?”
胡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的黑色小方块,上面连着一根长的天线。我拿在手里掂量了一下,很轻,几乎感觉不到重量。胡来抓着天线,折弯成一个椭圆形状连在了方块上。我才发现那根本不是天线,是固定这个方块用的绑带。
“这东西装猪身上哪儿?”我问。
胡来指指我的耳朵,示意我把方块贴到耳后的位置。
一阵优美的钢琴旋律在我脑中响起。
“这是带GPS定位的骨传导耳机。你现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D大调双钢琴奏鸣曲。”
“音乐我是一窍不通,给猪听这玩意儿?”
“对,从和牛养殖方法中学的。别人有音乐牛,以后我就卖音乐猪。”
“每头猪都配这,那得多少钱?”
胡来又神秘的眨眨眼,他生来严肃的国字脸上便有了种给人滑稽的感觉,但是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低沉,“不要钱,只要保存数据就行。我以前念书时的导师给我申请的,这产品在美国也是测试阶段,连山上发射信号的基站都不用我掏钱。”
“有了这东西,我就不用在山上再弄围栏圈地了。在电脑里发个指令,猪就能自己回栏。”胡来转身对他的员工说,“大山,加料时间快到了,你们先去把食槽填上。”然后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回外边儿。”
等大山他们几个人加完饲料出来,胡来让我把耳机又贴在耳朵后边,在笔记本电脑上一阵捣鼓。耳机里没有传来任何声音。可能是心理反应,我隐约感觉到了一阵细微的震动。
“没声音啊胡来。”
“哈哈,没声音就对了。猪能听到的声波频率能高到4万赫,比人多两万呢。这些指令都只有猪才能听见。”
边说着,屏幕上凌乱的红点纷纷动了起来,向猪舍形状的方块快速移动。不一会,山上就跑下来一群猪,数量有一百来只,有大有小,白白的身子,只有头和屁股尾巴是黑的,圆圆的甚是可爱。猪们一溜烟跑到食槽边欢快的进食,瞬时间猪声鼎沸。
“这批是金华的名猪——两头乌。肉好吃,也能加工火腿。白天全放山里散养,让它们自己在山上刨点吃食,傍晚回来加一次饲料。每天听两回音乐,绝对有噱头。”
我把耳机递还给胡来,一眼瞥到那白白黑黑的一群两头乌中间,夹杂着一个全黑的猪影,个不大,按猪的标准来说有点瘦弱。在食槽最边上小心的吃着饲料,偶尔还被边上的猪挤的摔在地上,爬起来抖抖腿又继续吃。
“咦,这里面怎么还有头东北大民?就一只?”
“是啊,送货的时候弄错了,混里面了,将就养着吧。”
“好像受了排挤,腿都有点瘸了。”
“来的时候是不瘸。不用管它,大了就杀,后面也不会有东北民猪了。时候不早了,我们一块去喝个小酒?”
“不了,小涛升了高中,在镇上上学呢。我拿了车顺便接他回村。”
“那行,过俩月你再来,挑只最大的杀了,拿回村里分掉。当是第一批音乐猪的广告,也算是回报乡亲们的福利了。”
离开的时候,我目光停留在了一只猪上。那只猪听着胡来和我的聊天,停止了进食。仰起头,仿佛在盯着我看。眼圈一周都是白的,像是反了个色的大熊猫。就叫它白眼吧,这头长相与众不同的猪,看了看我,又转头看了看那头全黑的东北民猪,晃了晃脑袋,也不吃食,就这样目送着我和胡来一行人离开。
回村路上,开着胡来给我配的金杯车,不,应该称它为分销商专用车。生计问题眼看着就能解决,我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小涛似乎也感受到了我内心的喜悦,雀跃的跟我分享他在高中的见闻。
“爸,我同桌叫李胜。他跟我说,pi,就是圆周率,包含了整个宇宙的秘密。”他说着说着手舞足蹈了起来,“在小数点后那数都数不清的数列里,你能找到你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如果转换成二进制,你甚至能在这无穷的数列里找到你的一生,你身边的一切。整个宇宙从诞生到现在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隐藏在里边。科学家已经在数列里发现了氢原子方程的沃利斯公式呢!”
“你坐着好好说,别拉我手,我在开车!”
“爸,李胜说,他要把圆周率背下来,一直背到人类的极限。说如果背成了,他就能掌握宇宙的真理了。”
“他是吃饱了撑的,计算器能算的玩意儿背它干啥。”
“我也想背。李胜说,有个日本人叫原口证,能背到小数点后10万位。”
“那他掌握宇宙的真理了吗?”
“我和李胜都觉得10万位还没到极限。可能突破人类的极限时就懂了。”
“你们这是悟道都来了。得,只要不影响分数,你爱干啥干啥。”
重复而又单调的日子便在我去镇上进货(五元猪成长期很快)和回村摆摊中度过。那段日子陈大爷还没到处跟人喊宇宙大爆炸和放电影的事,除了织布绣花就是坐在裁缝铺门口,抽着旱烟发着呆当我邻居。我空闲时也会跟他唠几句家常。
两个月很快过去,有天傍晚我又去了回广来养猪场。现在再去早已是熟门熟路了,登记完换好工作服,我直接去放养猪舍外面找到胡来。胡来正在指挥员工们清扫猪舍,充填饲料,见我来了,便递给我一根烟。
“效益怎么样?”我问他。
“非常好,非常好。就等这批音乐猪上市打响品牌了。你儿子上高中了成绩怎么样?”
“班里中上游吧,最近发了疯,整天和他一同学混在一起背圆周率。”
“叛逆期嘛,都这样。”
“这两个月跟你进货的肉钱是不是得跟你算算了,老是拿肉不给钱不是个事儿。”
“不急不急,等音乐猪品牌打出来再说。我不催你你就别急,安心卖着。”
一支烟的时间过去,大山他们都忙完出来了。胡来又拿起笔记本电脑给山上的猪们发送了指令。不一会,猪们便聚集在食槽前。
“大山,去把食槽边上的围栏圈起来,等会好抓。富贵哥,你看看,相中哪头?”
“你挑吧,你给村里请客,我可做不了主。”这时我的眼光又撇到了那只削瘦又带点瘸的黑色猪影,还是在食槽最边缘的地方小心翼翼的吃着。我感慨说:“那只东北大民,都没怎么长肉啊。”
胡来似乎没听见,指着中间一只体型最大,毛色发亮的两头乌说:“就那只吧,看着有200多斤了。”说着抓起套杆,丢给大山他们。大山很轻松的就把最大的那只两头乌勾了过来,跟几个人一起把它按到在地,开始用绳绑住四肢。那猪发出一阵悲鸣,却被淹没在群猪吃食的鼎沸声之中。这时我视线一扫,又看到在一群低头抢食的猪中间,有只猪停止了吃食,仰起头。是白眼,眼周一圈白色特显眼。它看着大山他们在绑那头猪,打了个响鼻,又晃了晃脑袋,转头盯着我跟胡来。在那个瞬间我好像看到它露出了一个像人的表情,嘴巴微微往上斜,露出了一排牙齿。
这时大山几个人已经麻利的把猪绑好,抬上了皮卡。胡来开车,带我沿着山脚开了几公里,拐了个弯,到了屠宰场。
“这音乐猪我都不让用电。电晕了再放血放不干净,还是人宰的肉质更好。”胡来对我说。
“我来。”
那头大猪在平台上挣扎着,似乎想挣脱大山他们的压制。我摸着脖子根上的位置,准备一刀捅进。这时我脑袋里突然闪过白眼盯着我的那个笑容。它在笑什么?是自己终会成为盘中餐的命运,还是在嘲笑人类的残忍?
“哎呀,不够深。心脏没破,血乱溅了。”胡来叫喊的声响和大猪临死挣扎的嚎叫把我拉回了现实,赶紧把刀拔出来,又照准原位置全力一刀捅进转了半圈,了结了大猪的性命。
“没事吧?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说着,胡来递给我一块毛巾。
我一边擦手,一边把白眼盯着我的那副笑容从脑袋里甩掉,说:“没事,就是突然有点走神。”
音乐猪在村里的评价非常好。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鲜美多汁,质嫩爽口,所有能评价肉的褒义词都能套到上面。胡支书脸上也洋溢着喜气,人人都夸他有个能干注定要发财的儿子。我的摊子上也撤了商品猪的肉,只卖广来牌音乐猪。因为胡来给我的价格很便宜,所以我卖价也不比商品猪高多少,生意很是火爆。
又过了俩月,隔壁的裁缝铺蔡大娘找上我,说娘家的一个后生结婚要摆席,让我去挑头音乐猪杀了带回来。
这回去厂里,胡来不在。矮个子大山接待的我。用电脑把猪招回栏之后,大山指着一只猪跟我说:“就那只吧。最近它长的最快。”我一看,是那头全黑带点瘸的东北民猪。奇怪了,这猪上次还那么瘦,怎么突然长这么肥了。我点点头,大山便让员工们开始套那头黑猪。这时我突然看到电脑屏幕上猪舍外边还有个红点在慢慢的接近。
“等下,这怎么还有头猪在外边?”
“兴许是山上吃太多,慢悠悠晃回来的。”
这时屏幕上红点已经到了猪舍里边,我往那个方向一看,白眼正站在食槽的围栏外看着我。隔着栅栏我都能看见它脸上又露出了和上次那个一摸一样的笑容,嘴巴微微上斜,露出一排牙齿。像是在嘲笑我奈何不了它。
“等下。”不知为什么,我瞬间变了念头,喊停员工们绑大黑猪的进度,抓起套杆每人发了一个。“先把食槽外的那只抓了,那只更大。”
白眼看到我们几个人人手一个套杆朝着食槽外边过去,一个支棱,眼神中露出了恐惧,打了个响鼻嗷嗷叫着往上山的方向跑。无奈上山的路早已被拦起,便叫喊着在猪舍四处乱窜。
我和大山他们东追西赶,终于把白眼一头套住,往食槽方向拖。准备拿绳索绑了丢上皮卡。白眼一路盯着我,一路狂叫,在靠近食槽的时候突然做出仰天狂吼的姿态,但是没发出任何声音。我隐约感觉耳朵微微震动,便回头一看,食槽栏里的所有二头乌都停下了吃食,转头往我们几人这里飞奔过来。
一百多头接近两百斤的猪,发了疯似的冲破围栏,嘶叫着笔直朝我们冲过来。大山赶紧拉着我往边上闪,大叫:“闪开,都闪开!”其中有个员工乍见这种离奇的情景,一惊之下,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猪群直接绕过,理都没理他,跑到白眼处,开始疯狂撕咬白眼。一支烟时间不到的功夫,地上全是碎肢烂肉。白眼被猪群活生生的吃了!
我当时浑身鸡皮疙瘩竖的都快炸了。白眼到死都在盯着我看。在猪群疯狂又杂乱的身影和步伐中间,一直有一道带着仇恨的目光从重重猪影中透出来,聚停在我身上。仿佛那种仇恨是实质性的鞭子,一鞭又一鞭的抽打在我身上。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惊和做梦都没想到过的诡异场景带来的压力,浑身湿透。
猪群终于安静了下来,分散开退回了猪舍,仿佛无事发生过一般,倒地便睡。我和大山强打精神,把撞掉的围栏装了回去。大山看着满地的残渣和被绑到一半的大黑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用眼神在询问我该怎么办。
“把这只黑猪绑了运去杀了吧,我带回去。”我有点无助的说,“这事我会跟胡来汇报,损失我担。”
我心事重重无精打采心不在焉的回到了村里,也不管小涛是不是和李胜在客厅一个劲的背着圆周率,跑进厨房坐下狂灌了许多酒,便躺到床上睡。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我第一回梦见我那不见了十二年的媳妇。
儿时杀猪说说(杀猪的经典说说)3
年味儿之杀年猪
“红萝卜,咪咪甜,看到看到要过年,娃儿要吃肉,大人没得钱。”当一群孩童拍着手唱着这首儿歌的时候,我知道,要过年啦!那时的我,完全领会不到儿歌中所说的“娃儿要吃肉,大人没得钱”的心酸,只是无限盼望着年的到来。穿新衣、吃嘎嘎、走人户、得压岁钱……那时的年,让人无限向往。过年的准备,就有了很多的仪式感。在那样一个“到口的肥肉给人换骨头,总不心甘”的缺少油荤的年代里,第一盼望的当属杀年猪了。
冬至一过,就是杀年猪的时候了。家家户户都养了一头猪,小春的红苕挖回来,把猪催得肥肥的。提前联系好杀猪匠,定好了日子。那天,早早就烧好一大锅开水等待。灶里,是平常都舍不得烧的干柴,熊熊的火焰得保证锅里有源源不断的开水。
当养了一年多的大肥猪看见圈门被打开的时候,它也感觉世界末日的来临,赖在圈里不肯挪步。于是,杀猪匠在前,用大铁钩子勾住猪耳朵,主人家在后抓住猪尾巴使劲把猪望外边推,伴随着猪绝望的嘶吼,它终于被按在了案板上。杀猪匠眼疾手快,“快准狠”,剔骨刀往猪脖子下一捅,鲜血喷薄而出,直接流到地上放着的旺盆里。鲜血流尽,猪也就气息奄奄了。杀猪匠用手在旺盆里搅拌搅拌,让主人家端到一边去放着,等血液凝固以后在划成一坨坨的,倒锅里慢慢烫熟(这个工序,锅里的水是不能沸腾的,那样猪血旺会有气泡,就不好吃了)这时,杀猪匠会在猪后腿的蹄子处用刀划拉一道口子,喊一个人拿着捶洗衣服的棒子,有节奏的敲打猪身,他则鼓足气,两手捧着猪蹄,从刚才划拉开的口子开始吹气。一人吹,一人捶,慢慢的猪越来越大,等整个鼓足气的时候,猪的四肢已经完全张开,肚皮滚圆滚圆的,它的体积,足足是先前的两倍。地上垫上稻草,把猪放来趴在草上,旁边放一张桌子,桌上置一个大木桶,先前烧好的开水这时就派上用场了,桶里加满水,用一根细细的橡胶管把热水引出来,流到猪的身上去。从猪头开始淋,一边淋一边用手去扯毛,等把长长的猪鬃毛扯完了,拿一根灯草拴好,喊主人家拿去放好,等着卖一个好价钱。然后拿着刨刀,开始从猪头到猪尾顺着方向使劲刮,在刺啦刺啦的声音中,猪变得雪白雪白的,真正是“一次不挂”了。
主人把梯子拿出来撑在房檐下,杀猪匠用铁钩勾住猪后腿,把猪倒吊起来。开膛剖肚,取出猪肚子里的心肝肺肠等部件,主人家就拿着大肠到一边去打整了,等会儿是可以炒两盘的。小袋子(猪小肠)照例是用灯草拴好挂起来,等第二天装香肠要用的。如果猪平常吃得好,足够大,从肚子里掏出来的边油会装满一筲箕的,等完全冷却了,再加一些肥肉熬油,那就是未来一年的炒菜用油了。杀猪匠把开膛破肚的猪翻过来,从猪背开始下刀,称为“开边口”,把猪砍成两半,只听着“嘭嘭嘭”的声响,之前还活蹦乱跳的猪,已经变成一块块的肉,在萝篼里堆着了。如果主人家的岳丈岳母还健在,照例是要砍一个大大的肘子下来,等正月初二回娘家的时候,提回去孝敬老人的。
杀猪匠的工作至此完成,可主人家的事情才起了一个头儿。杀年猪那天,是要请亲朋好友和街坊四邻吃“旺子汤”的。熬一大锅萝卜汤,里面加上隔子肉、粉肠、血旺,那个味道,简直不摆了。萝卜的甜味儿,加上肉香,就是无与伦比的美。肥肉薄薄切片,稍微煎一下,形成“灯盏窝儿”,放上自家地里的蒜苗,比今天的回锅肉香了不止百倍。再炒一份瘦肉,两三个青菜,就是待客的盛宴。今天的主角当然是“旺子汤”,吃完了又添满,主任家一直来忙碌,客人们推杯换盏,吃得满嘴流油,心满意足。顺便再说说今年的收成,谈谈明年的干法,这样的日子,最是惬意不过了。
那大半个月的时间,大部分家庭都在杀年猪,于是吃“旺子汤”就成了大家相互联系感情的最好的活动,大人谈的是家国天下事,而我们只关心,明天是不是又可以吃嘎嘎了。因为家里杀的年猪,已经进了大缸,被腌渍成腊肉,要留着过年、正月待客和未来半年的解馋了。有感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