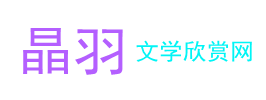关于铁匠的美文
铁匠 陶浒 绘
上世纪70年代,我国经济远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在我的家乡临潼渭北农村一带,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不少东西,比如锅灶上用的刀铲,舀水用的瓢,干活用的铁镐、公式头、锄头,犁地用的铁犁、铁铧、耙齿等,大都出自铁匠之手。因此,那个时候,几乎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一两名铁匠。
当时,我们村里就有一个铁匠,手艺特别好,方圆十几里,人人皆知。他长得虎背熊腰,一对铜铃眼,络腮胡,方面大耳,一年四季都留着光头,一米八的大个子,麦色的皮肤,站在人面前仿佛是座铁塔。村里娃都管他叫铁匠叔,至于他的官名却不得而知。我跟他的小儿子是小学同学,所以常有机会到他家里去玩,还能专门看他打铁。
在他家前院围墙右拐角,用几根木椽搭了一个简易工棚,上面苫了六七页石棉瓦,就算是他的打铁作坊。石棉瓦下面,靠西墙有一个风箱,一个火炉,一个铁锛子,三把铁锤,四五个长把铁钳子。棚下靠近木柱处,左手边放着一口水瓮,里面时常蓄满清水。
风箱后边墙旮旯处,摆放着一堆平时收回来的废铁,这也算作是原材料吧。尺寸有长有短,形状有片状的、块状的、条状的,还有一些少角没棱的,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主人发落。
铁匠叔平日在生产队干活,要是谁家的公式头、锄头、刀铲有了问题,都会找他修理。生产队的铁犁、铁铧、耙齿等要是用坏了,就直接让铁匠叔带回去修补,队上给他记点工分。另外,再给予适当的补贴,作为原材料费用。
每当秋季收完玉米,种毕小麦,农活也不多了,大家就慢慢闲了下来。直到过年前的这段时间,都是铁匠叔最忙的时候。他一忙起来,大儿子就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当然,铁匠叔的媳妇兰花姨也会帮他干些拉风箱、填炭之类的活。
一个冬日,我吃过早饭,便去铁匠叔家找他的小儿子东东玩。刚进他家大门,就见东东双手抓着风箱拉杆,“呼啦呼啦”地拉着风箱,铁炉上的火苗“呼呼”作响。一块铁在火苗的裹挟下备受煎熬,由于热胀冷缩,不时发出“嗞嗞”裂响,颜色渐渐由黑变红。铁匠叔和他的大儿子,各系一条颜色发黑的皮围裙,上面不少地方被火星灼烧,留下许多大小不一的窟窿。
火炉上的那块铁被烧到遍体通红。铁匠叔凭着经验,觉得火候已到,便用左手握住一把长柄铁钳夹出铁块,并快速放到铁墩上。右手十分熟练地操起一把小铁锤,并用眼睛示意大儿子拿起大铁锤,引导着他在烧红的铁块上“叮叮当当”捶打。听他们父子打铁的声音,那简直像是在欣赏一首美妙的钢铁演奏曲。
儿子抡起大锤,沿着父亲小锤行走的足迹,一锤压上一锤,在烧红的铁块身上反复敲打。父子俩抡起铁锤,在头顶画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也画出了打铁人生命的轨迹。正是这不断的敲击,铁块按照主人的意志,发生着微妙变化。伴随着“叮叮当当”的音乐,铁块的品性也一步步从幼稚走向成熟。
铁匠叔突然停下来,将铁块重新夹进炭火里,东东又开始卖力地拉起风箱。他们父子仨的配合十分默契。半袋烟的工夫,铁匠叔又将铁块从火中夹出,随着一声“快点”,父子俩又“叮叮当当”在铁墩上敲打起来。铁锤一次次落下,溅起一片片四射的火星。
那口盛满清水的大瓮,此刻正静静地等候着,等候着烧红的铁器来造访。每一次造访,都决定着一个即将成形铁器的命运。铁匠叔说这个叫“蘸火”。每当“蘸火”时,他都用长钳夹着滚烫的铁伸进水里,伴着“嗞啦嗞啦”的声响,水面冒出一股白烟。“蘸火”时间是否恰到好处,决定着这次铁器制造的成功与否。在铁匠叔常年这样敲敲打打下,村里人家便有了锄头、镐和公式头等工具。乡下人有了这些铁器,在那个靠农具跟土地打交道的年月,一块块土地,在一年四季的轮回里,才被描画成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由于铁匠叔手艺好、人实诚,打制出来的铁器结实耐用,因而他作坊的生意十分红火。这样的光景,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农业现代化程度逐年提高。拖拉机取代了畜力,农村人建房,渐渐用钢筋混凝土代替了木椽木檩。就连锅灶所用的刀、铲、瓢等,也纷纷被不锈钢替代。到上世纪90年代初,铁匠叔的生意日渐式微。后来,他把铁炉拆了,其铁匠身份也就有名无实了。如今,上了年纪的铁匠叔,身体依然硬朗。每当我回村看到他,都会勾起我对他那段打铁生活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