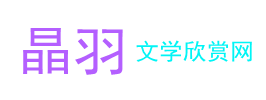说说比赛话(拉丁舞比赛说说)
罗马当着当着拉丁联盟老大,怎么就和小弟们撕了起来?,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逗比鱼的大千世界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说说比赛话(拉丁舞比赛说说)1
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拉丁联盟?
公元前五世纪,拉丁城邦没有一个中央政府,但是为了防御他人侵入,他们只能抱团建立了一支武装力量。作为最大的联盟成员,罗马自然而然地扮演起领导的角色。然而,随着时间地推移,拉丁联盟城邦周围的威胁越来越少,而内部的罗马势力却越来越大。这使得拉丁联盟的小城邦们忐忑不安,他们害怕罗马在与周围势力征战的时候将他们的地盘一并吞走。
他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若是没有高卢人入侵罗马的大事件发生,他们的联盟早就四散了。谁让大家都是一个语系的城邦呢,为了防止高卢人对所有拉丁城邦侵袭,大家又团结起来,与罗马抱团。当然,这其中不包括罗马的老敌人提布尔与尼斯特。罗马当然很不高兴,于是与两个城邦打了起来,直到把他们打服了为止。
然而,这样的暴力征服很快将拉丁联盟拖入更不和谐的地步,很快,在公元前349年,高卢人再次攻打罗马的时候,他们拒绝再向罗马提供军队支援。甚至,在公元前343年的时候,拉丁联盟打算攻打老大罗马。不过,就在这一年,罗马人和隔壁萨摩那人打起架来了(地图中西瓜红色的就是罗马,深绿色的为萨摩那)。这一打,把小弟们给惊傻了,这啥情况,打仗也有人和他们抢先,于是他们改变了作战方案,放弃了罗马城,转向另一个国家。
小弟打老大的戏码终究是没有上演。
罗马与萨摩那人的战争片演了两年,两年之后,战争片结束散场。小弟们左右一看,觉得有机会往输的一方萨摩那那头占点便宜,于是拉了坎帕尼人就开始打萨摩那人。这就是典型柿子挑软的捏。他们组成的纵队出发后并不好好打仗,而是抢人东西,抢来抢去,抢得萨摩那人就跑前敌人罗马那儿告状。说是瞧瞧你的联盟成员,来踩我地盘了。
萨摩那人一定是没有读过《罗马协定》,拉丁同盟里的这项协定中,罗马并没有权力去阻止拉丁同盟国出去打仗。不过,罗马人心想着不能让隔壁这个二货知道拉丁联盟里的那些小弟都已经不搭理自己了,也不能让拉丁联盟停止进攻,因为这样的话,会让这些联盟小弟疏远自己。都没小弟了,这盟主当的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罗马必须捣浆糊。坎帕尼人看出了端倪,于是就煽动起拉丁联盟的小弟,小弟们心下琢磨,想出了一套“声东击西"的计谋(显然,在没有中国兵法流传的拉丁人地界,这样的战略战术也能无师自通),他们同坎帕尼人私下商议,表面上他们要打萨摩那,实际,他们要攻打的对象是罗马。
然而,这一次的密谋风声走漏了。所以说,一定要保持队伍的一致性,任何有异心的人都会导致整个计划的失败。拉丁联盟的这些小弟刚要开始起事,地区执行官(类似于拉丁联盟裁判官)提早结束了任期,新的人选上台了。而这一次被选上去的,是两位罗马人:提图斯-曼利乌斯与普布利乌斯·德西乌斯·穆斯。
(普布利乌斯·德西乌斯·穆斯)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罗马人作为拉丁地区行政官,掌握了话语权,任何联盟出兵都得经过行政官同意。这么一来,小弟们总不能说打罗马吧?可偏偏他们就是有点脑子不好使,派了十个人跑罗马那儿说事儿,说自己要攻打萨摩那之类的话,其中有两个领导,一个叫阿弥努斯,一个叫努米苏斯。阿弥努斯在会议中朝罗马人抱怨,说是罗马人不把拉丁同盟里其他城邦当自己人看待,而是当成了小弟(当然,其实他们个个都清楚自己就是小弟),接着又说罗马人不给他们政府席位。罗马人也不和他们纠缠,在宙斯神庙前当众告诉他们不要去攻打萨摩那,因为他们与萨摩那人已经结成联盟。阿弥努斯自然不肯罢休,据说在神庙那儿就开始叫嚷,由于这样的做法亵渎了宙斯神,忽而,一阵风刮来,阿弥努斯踉跄摔下台阶死了。看到阿弥努斯摔死,罗马就向公众宣布要驳回拉丁同盟的军队,因为神惩罚了拉丁的特使。
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拉丁与萨摩那之间的战争,而罗马的公民却为之大声喝彩。
公元前340年,罗马与萨摩那联盟在现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那儿交战,并战胜了对方。先前说的曼利乌斯为了严肃军纪,还杀死了儿子。
(杀死了儿子的曼利乌斯)
接着的两年,在特里法努,罗马人再次重创昔日的联盟小弟。整个拉丁联盟就此瓦解,部分城市归入罗马,部分称为罗马执政的半罗马城邦模式,还有些就直接成了罗马的殖民地。结束了拉丁联盟之后的罗马共和国,也开始走向向外扩张的道路。
与热闹的希腊半岛不同,古代意大利地区的人总在拖泥带水中曲折壮大,即便是到了现代,意大利人的这种风格仍旧存在延续着。
最后还想评价下那些拉丁小弟,大腿虽瘦,胳膊还是拗不过大腿的。
喜欢这类文章的,记得关注今日头条“逗比鱼的大千世界”。
说说比赛话(拉丁舞比赛说说)2
这是一个下着雨的夏天,可偏偏有太阳,吃完中午饭溜达在热闹的锦华市场!想着买点啥水果呢?突然听见音乐声,哪里呢?原来是一楼门市有上舞蹈课的教室,敞着门,里面人还不少,都是大叔大妈的!顺眼一看节奏感还挺强,原来是拉丁舞,后来我才知道恰恰恰!停下来的时候一位大哥问我,小伙子想学拉丁舞吗?我一想也真没啥事还下雨,进屋看看也好,避避雨!吐岁恰恰万,一位女老师喊着节拍,随着音乐十几位舞者跳着基本步,很整齐,可以跟着跳,边跳边学,边上的大哥一边扇着扇子一边擦着头上的汗和我说,于是我就穿着大裤衩子,拖鞋,加入恰恰恰的队伍中,开始了我的拉丁旅途![大笑][大笑][大笑]
我的朋友们你们学拉丁有什么奇遇?可以留言给我说说!我也会继续讲我和拉丁舞的故事给粉丝们[灵光一闪]
说说比赛话(拉丁舞比赛说说)3
【向人民学习 向生活学习·重温当代现实主义经典作家】
作者:邢小利(陕西白鹿书院院长)
陈忠实是当代现实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白鹿原》也是当代现实主义的经典力作。从《白鹿原》上回望陈忠实走过的创作之路,似乎可以这么说,陈忠实《白鹿原》之前的所有作品,都是为写《白鹿原》做准备的——生活的、人物的、思想的、艺术的准备,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等到完成《白鹿原》,登上广阔的一望无际的高峰,陈忠实看到的是山高水长。
《白鹿原》写作之前,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从1973年11月在《陕西文艺》发表的《接班以后》起,到1988年6月完成、刊于《鸭绿江》1989年第1期的《害羞》止,共写了54篇;中篇小说从1981年1月开始写《初夏》(刊《当代》1984年第4期)起,到1988年1月在《延河》发表《地窖》止,共写了9部。从这些作品看,陈忠实的创作已然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点,植根生活深处,紧扣时代脉搏,每一篇、每一部作品,都有作家的现实关切,都表现出作家对生活、对时代的发现和思考。这是陈忠实走向《白鹿原》、走向广阔而深厚的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基础。
陈忠实不是一个天才型的作家。“文革”前,他二十三四岁的时候,靠自学,在地方报纸发表了十来篇诗歌、散文、故事等习作。1973年,31岁那年,他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此后一年一篇,到1976年在刚复刊的《人民文学》第3期上发表《无畏》止,连续发表了4篇短篇小说,在当时颇有影响。但诚如他后来回忆总结的,这些作品很不成熟,他都不好意思再看。不过,这些写作实践也让他锻炼了直接从生活中选取素材的能力,锻炼了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演练了结构和驾驭较大篇幅小说的基本功。
1978年,陈忠实由公社转到文化馆工作,开始了艰苦的自我反思和艺术探索。如果说,他在“文革”后期的写作,是踉踉跄跄地跟着潮流走,那么,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创作,则是在迷茫中探索,在探索中发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逐渐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
陈忠实创作的转变,从1978年开始,到1988年完成,历时十年。这个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称为通往《白鹿原》之路,他的中篇小说《初夏》《康家小院》和《蓝袍先生》为其路标。从这三部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陈忠实创作探索和变化的轨迹,也可以看到他在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上,不断走向开阔与丰富。如他所言:“八十年代发生的一切,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太重要了,太不容易了,太了不起了。对于经历过这一变革全过程的我来说,也是一次又一次从血肉到精神再到心理的剥离过程。这个时期的我的中、短篇小说,大都是我一次又一次完成剥离的体验,今天读来,仍然可以回味当时的剥离过程中的痛苦与欢欣。”
第一个阶段,陈忠实的小说创作紧紧追踪时代的脚步,关注时代与人的关系,注重描写政治与政策的变化给农村社会特别是农民生活、农民心理带来的变化,或者反过来说,是通过农民生活特别是农民心理的变化来反映政治的革新和时代的变化。他的小说侧重在人物冲突中揭示社会问题,在性格描写中展示人物的道德品质,并隐隐以道德标准来评判人物。
《初夏》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家庭父与子的故事。离开还是坚守农村,考虑个人前途和利益还是带领大伙走共同富裕之路,在这个人生选择问题上,父亲这个农村的“旧人”与儿子这个农村的“新人”发生了激烈的无法调和的冲突。父亲冯景藩,是冯家滩的老支部书记,几十年来一直奋斗在农村基层,把一切都献给了集体化事业,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觉得以前的工作白干了,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于是,走后门让儿子到城里工作。不料儿子冯马驹放弃了进城的机会,决心留在农村带领大伙“共同富裕”。
这是一个中国社会历史转型初期的故事,陈忠实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也正在转变的过渡之中。他在与写合作化题材的著名作家王汶石的通信中说,他写这部小说,期望“用较大的篇幅来概括我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着的农村生活”,但他写得很艰难。他1981年1月写了《初夏》第一稿,寄《当代》杂志,编辑让他一改再改,3年间3次修改才完成,刊《当代》1984年第4期。陈忠实说,“这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部中篇,写作过程中仅仅意识到我对较大篇幅的中篇小说缺乏经验,驾驭能力弱。后来我意识到是对作品人物心理世界把握不透,才是几经修改而仍不尽如人意的关键所在”。“对作品人物心理世界把握不透”,实际上反映了作家在新时期思想认识上的某些局限性。陈忠实写冯景藩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负担”和“失落”情绪,真实且有时代的典型意义,反映了作者对于生活的敏感。但他这时的艺术思维,受十七年文学影响所形成的心理定势还未完全消除,他还习惯以对比手法塑造与“自私”“落后”的冯景藩对立的另一面,即乡村新人形象冯马驹,这个人物不能说在现实生活中绝无仅有,但他显然是作者艺术固化观念中的一个想象式的人物,缺乏历史的真实感和时代的典型性。
《初夏》的艰难写作特别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变化引发了陈忠实的反思,他后来称之为思想和艺术的“剥离”。他明白,他自身需要一个蜕变,一个文化心理上的和艺术思维上的深刻蜕变。“剥离”的同时还要“寻找”,这是陈忠实20世纪80年代前期必要的思想和艺术的蜕变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后来的陈忠实,也就没有《白鹿原》。陈忠实说:“作家毕其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因为小说创作是以个性为标志的劳动,没有个性就没有文学。”“剥离”与“寻找”,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没有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剥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寻找”;而要“寻找”——寻找到陈忠实借用海明威的话来表述的“属于自己的句子”,就必然要经历这个“剥离”过程。这是一个鱼跃龙门的过程,也是一个化蛹为蝶的过程。“剥离”是精神涅槃,“剥离”的过程也是一个“拷问”自己的过程,陈忠实说,他的这种“剥离”意识从1982年春节因现实生活触动开始,贯穿整个80年代,“这种精神和心理的剥离几乎没有间歇过”。
民族文化之根应该寻找,但这个根不应该在深山老林和荒郊野外,而应该在现实生活中人群最稠密的地方
陈忠实走向《白鹿原》的第二个阶段,是他认识到了文化与人的重要关系,也开始了文化与人的艺术探索与文学表现。
1982年,陈忠实写了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康家小院》写一个“生就的庄稼坯子”的农民勤娃和他新媳妇玉贤的故事。玉贤上冬学时被杨教员的文化气质所迷,更被杨教员所传授的文化和思想启蒙,与之有了私情。玉贤在挨了勤娃的打骂、父亲的打骂和母亲的生活劝导之后,去找杨老师希望兑现“婚姻自由”的思想启蒙,不料杨教员却显出了叶公好龙的本相。玉贤由精神的某种程度的觉醒,到经历了人生的痛苦和迷乱,而后又有所觉悟,她看到了生活的本相,也真切地认识到了自己人生的位置。玉贤的悲剧是双重的:没有文化的悲剧和文化觉醒之后又无法实现觉醒了的文化的悲剧。陈忠实写这部中篇,与他1981年夏去曲阜参观了孔府、孔庙、孔林有关,在那里,他对文化与人的关系深有感触,由此生发而孕育出了这部小说。《康家小院》开始关注文化与人的内在关系。陈忠实此后的小说不断触及文化与人这个命题,1985年写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从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写人,1986年写的中篇小说《四妹子》从地域文化入手写人,最后在《白鹿原》中全面地完成了关于文化与人的文学思考。
《蓝袍先生》是第三个路标。此作写于1985年。在此之前,陈忠实的小说基本上是密切关注并且紧跟当下的现实生活,而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历史人物”。蓝袍先生徐慎行的性格和命运从新中国成立前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后,在描写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展现这个人物命运的时候,特别是发掘这个特意把门楼匾额“耕读传家”的“耕读”二字调换成“读耕”的人家的时候,这个幽深的宅院以及这个宅院所折射出的民族文化心理的隐秘,让陈忠实久久凝目并沉思。关于长篇小说的一个若有若无的混沌景象在陈忠实脑海中浮现,他也就此萌发了创作《白鹿原》的念头。《蓝袍先生》写文化观念对人行为的影响,写传统礼教与政治文化对人的束缚。这部小说给他打开了一扇门,他开始关注并研究历史的乡村,酝酿创作上的重大突破。
创作之外,陈忠实在80年代中期的广泛阅读,对他的思想和艺术也颇有启迪。他读当时广被介绍的拉美文学,读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昆德拉启示他,创作重要的不是写生活经验,而是写生命体验;他读国内的“寻根文学”作品以及与这一文学和文化思潮相关的理论和评论。为了增强未来小说的可读性,他还阅读了大量外国的畅销小说。
他在《世界文学》1985年第4期上读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大师、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中篇小说《人间王国》,还读到同期杂志配发评论《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的寻踪者》。陈忠实读后不仅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而且从卡彭铁尔艺术探索的传奇性经历中获得启示。卡彭铁尔早年受到欧洲文坛各种流派尤其是超现实主义的极大影响,后来他远涉重洋来到超现实主义“革命中心”的法国,“但是八年漫长的岁月却仅仅吝啬地给予卡彭铁尔写出几篇不知所云的超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灵感’”。卡彭铁尔意识到自己若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彻底改变创作方向,“拉丁美洲本土以及她那古朴敦厚而带有神秘色彩的民族文化才具有巨大的迷人魅力,才是创作的源泉”。卡彭铁尔后来深入海地写出了别开生面的《人间王国》,被小说史家称为“标志着拉丁美洲作家从此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卡彭铁尔对陈忠实启示最深的,是要写“本土”,但当他真正面对自己“本土”的时候,他对自己熟悉乡村生活的自信被击碎了。陈忠实有相当深厚的农村生活经验,他曾经说他对农村生活的熟悉程度不下于柳青,但他所熟悉的农村生活,主要是当代的农村生活。他感觉自己对乡村生活的认识太狭窄了,只知当下,不知以往,遑论未来。他意识到,对一个试图从农村生活方面描写中国人生活历程的作家来说,自己对这块土地的了解还是太浮浅了。
陈忠实对“寻根文学”的理论和创作极有兴趣也极为关注,但他很快发现,“寻根文学”发展的方向有了问题,一些人后来越“寻”越远,离开了现实生活。陈忠实认为,民族文化之根应该寻找,但这个根不应该在深山老林和荒郊野外,而应该在现实生活中人群最稠密的地方。
陈忠实关注文坛动向,喜欢读文学评论。在读当时的一些文学评论时,他了解并接受了“文化—心理结构”这个从哲学转为文学的理论。这个理论给他的创作启悟是,人的心理结构是有巨大差异的,而文化是人的心理结构形态的决定因素。认识到这一点,陈忠实的创作思想就从人的性格解析转为对人物心理结构的探寻。“文化—心理结构”说影响陈忠实小说表现技巧的一点就是,他在后来《白鹿原》的创作中,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对人物肖像的外在刻画,而注重描写人物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
生活不仅可以提供作家创作的素材,生活也纠正作家的某些偏见
如此一路走来,陈忠实就登上了历史上的“白鹿原”。为写这部他称为“死后垫棺做枕”的作品,他从1986年到1992年,两年准备,四年写作。
准备期间,陈忠实读了一些历史、哲学和心理学著作。如王大华写的《崛起与衰落——古代关中的历史变迁》、北宋哲学家张载及关学的有关著述及研究著作。《白鹿原》书中所写关于乡民自治的乡约,最早就是在北宋由吕氏兄弟制定的,吕大钧和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等,都是理学分支关学的重要人物。
陈忠实重点去蓝田县、长安县查阅县志,还读了咸宁县(历史上西安府所辖县,民国时期取消,并入长安县)县志,查阅地方党史及有关文史资料。选择长安、咸宁和蓝田这三个县了解其历史,是因为这三个县紧紧包围着西安。西安是古都,曾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陈忠实认为,不同时代的文化首先辐射到的,必然是距离它最近的土地,那么这块土地上必然积淀着异常深厚的传统文化。查访过程中,不经意间还获得了大量的民间轶事和传闻。就是在这种踏勘、访谈和读史的过程中,陈忠实新的长篇小说的胚胎渐渐生成,并渐渐发育丰满起来,而地理上的白鹿原也进入他的艺术构思之中,并成为未来作品中人物的活动中心。一些极有意义的人物,也从史志里或传说中跳了出来,作为文学形象渐渐地在陈忠实的脑海中活跃起来。朱先生就是以蓝田县清末举人牛兆濂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白灵也有原型,原型是白鹿原上的人,是从党史回忆录里找出来的;田小娥则是从蓝田县志的节妇烈女卷阅读中萌发历史思考而创造出来的。
《白鹿原》创作期间,陈忠实一直住在乡间老屋。平常,像蒲松龄在村口摆个茶摊邀行人喝茶讲故事一样,陈忠实也想着法子与村子里祖父辈的老人拉话。他或者上门到别人家里,或者请人到自己家里,让老人们随便谈。白嘉轩这个形象,就是在同他陈姓门中一个老人交谈中触发灵感形成雏形的。陈忠实还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构思、想象、丰富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白孝文的一些故事就来自他当年在人民公社工作时一位青年干部的故事。在两年时间里,在这种与老人的交谈和史志的阅读中,陈忠实感觉自己的思维和情感逐渐进入了近百年前的属于他的村子,他的白鹿原和他的关中。
写《白鹿原》,陈忠实思想上非常明确,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需要坚持,同时也需要丰富和更新。现实主义创作需要生活,也需要艺术的勇气。写作过程中,他曾致信友人,说“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的全部能力而为之的”。同时,他也拿出了全部的艺术勇气。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陈忠实说:“我已经感觉到了许多东西,但仍想按原先的构想继续长篇的宗旨,不作任何改易。”“我已活到这年龄了,翻来覆去经历了许多过程,现在就有保全自己一点真实感受的固执了。我现在又记起了前几年在文艺生活出现纷繁现象时说的话:生活不仅可以提供作家创作的素材,生活也纠正作家的某些偏见。”
《白鹿原》是“文化心理”现实主义,它从民族的文化心理切入,写以儒家思想和文化为主体的乡土社会的秩序的崩溃和瓦解,写新文化进入中国后对社会生活以及各类人的影响,写白鹿原上新旧文化的冲突,分别受新旧文化教育和影响的新人和旧人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不同的人生追求。《白鹿原》画出这个民族的魂,进而探寻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大问题,不愧为当代的一部经典巨著。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2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