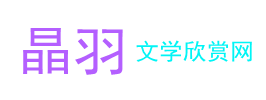关于蚕牙的美文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这两句俨然成了专门描述教师的诗,但我总觉得,那只是生硬的迁就,李商隐并不是拿它写给老师的,况且也太残酷,如果让我选一首的话,我会选王冕的“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香。”
以前小学有门课,现在不知是否还有,叫做《劳动》,课本封面上是圆头圆脑的小男孩小女孩,在给向日葵浇水,地上还放着小铲子小水桶。
这门课大多是讲手工、节约、小发明、种植的粗浅知识,比如用废弃罐头做花盆,自制显微镜、湿度计之类。
也有一课,是讲如何养蚕。
上完这一课,我放学回家后也央着妈妈给我弄点蚕来养,自己则开始准备火柴盒、棉纱和桑叶。
第二天,妈妈带回来一张旧的《人民日报》,她把报纸给我看,一面上洒满了芝麻般的小黑点,那就是蚕的卵了,在阳光下看的话,隐约有点儿透明。
这报纸上的蚕卵很多,我撕了一小片下来,就足够养一火柴盒了,剩下的不知道怎么办,就丢进水槽冲走了,隐隐听到沙沙的声音,像下雨似的。
那一小片上,我数了几次,不是22就是23,塞进火柴盒里捂着,妈妈说过两天就会出来了,问我桑叶备好了么,我拿出厚厚的一叠,还没有蔫。
桑叶是找同班的女生要的,她住在黑獐村,脸也黑黑的,笑起来牙齿很白,姓孟,叫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
孟同学家里是做裁缝店的,她五次三番地劝说我去她们家店里做条裤子,但我没去。
黑獐村的桑叶很有名,当地养蚕的人很多,老人们都会土法煮蚕茧抽丝,做成绸缎,后来改革开放了,就不再自己抽丝了,蚕茧都卖给南方人,南方人再做成绸缎卖回来。孟同学说,她家的店是仅存的两家自己养蚕抽丝纺绸裁剪的店面之一了。
我便问她另一家怎么样,她很不屑地说了一大堆另一家的不是,我也不懂,只是要了些桑叶。
孟同学很得意地说,这是她偷摘的隔壁家桑园的桑叶,那家的桑叶确实长得好。
“大概他们家屎尿多吧!”她愤愤地说。
那时我还住在柳镇上,没有搬到固城去,从家下来,一条直路通向小学校,大人们也放心孩子安全,极少有接送的,不像现在。
我下楼的时候碰见莉莉,举着火柴盒特别炫耀的告诉她我养了蚕。
“把你家老猫看好点,”我装模作样的警告她,“别去偷吃我的蚕宝宝。”
她一副好笑的表情:“得了吧大河,你养的又不是千年金蚕。”
老猫在楼梯上,转头瞪了我一眼。
我跑跑跳跳去了学校,外套口袋里装着火柴盒,手汗把纸面都沁软了,我赶紧抽出来,在春风里吹。
在校门口看见了傲雪。
傲雪是我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所见过的最美的女孩子,她站在那里,那里就有了一束光,从晴空直降,把她瓷娃娃般的肌肤映照到我眼睛里,深棕色的齐耳短发,眼睛也是,唯嘴唇嫣红,她笑起来,我的宇宙都在摇晃。
我气喘吁吁的站在校门口,跟她打招呼。
“大河。”她微笑着问好,眼睛弯弯,“别忘了下午要去播音。”
我怎么会忘呢,我们是多年搭档——虽然我那时候才九岁,但是我们已经搭档两年多了。
我点点头,一声不吭地快步走过去,超过她,然后在花坛的冬青树后面藏好,偷偷看着她去教室,她像林地中一头鹿,但不是蹦蹦跳跳的小鹿,而是优雅文静的少年的鹿。我从没见过她失去风度的时候,从来没有。
傲雪推门进教室,我才紧跟着进去,我们是同班同学。
我上课的时候从不认真听讲,特别是语文课。
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发下新课本,我用一个白天读完语文书,就可以扔了,整个学期都在玩,期末考试照样第二名。
第一名是傲雪,当然是我让着她的,她从没发现。
不过,今天我小小的心脏里并不全是她,还有那么一小块,是关注着蚕宝宝的成长,等待,对我来说是很缓慢的煎熬。
一堂课45分钟,我差不多每分钟都要偷偷把火柴盒打开看一下,阳光从玻璃窗透过来,那些蚕卵莹洁似玉,微微发光。
我是全班最矮的,就坐在第一排,我自以为用书挡着,老师就看不见了,多年后才知道,老师在上面,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的学生,在做什么,一目了然。
那位语文老师叫马红霞,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带我们,她家跟我家沾亲带故,对我也比较照顾,马老师早就盯着我呢,可我还在出神。
“肖大河,你说说,‘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这句表达了诗人的什么感慨?”
我收好火柴盒,站起来说:“光阴易逝,韶华虚度,聊以自慰之言,则做飞雪——”说到这个字的时候,我的心一跳,想到了傲雪。
马老师看我说不上来了,就说:“杨花轻浮空白头,榆荚干瘪无果实,这两句表达了诗人对一些只注重外表,但没有真才实学的人的感慨,他们生命的光辉,也只是那一瞬间的飘扬。同学们,现在布置一下课后作业,肖大河,这次你也要交。”
教室里发出轻笑,我是语文课代表,但我长期不交作业。
布置完作业,马老师说:“中午到我家来一下。”
她低头收拾教案,我趁机回头对全班做了一个鬼脸,在他们的哄笑中,下课铃敲响了,我盯着傲雪,她脸上露出那种责备和赞许的混合表情。
教师办公室是联排五间屋子,起脊的那种,马老师家就在办公室后面,有三排房子,都是教职工宿舍。
我去过她家,她老公是体育教师,倒也认得我。
中午去的时候,马老师一家人正在吃饭,攘着我也吃点,我很不习惯在别人家吃东西,就坐在一边等着。
吃完以后,马老师让我坐好,她拎出一架录音机,跟我说:“肖大河,县里有个小学朗读比赛,我找好范文了,你照着念就行。”
她教我用录音机,红色的按钮是录音的,念完了再按一下让它弹起来,再倒带回放。
我很快就学会了,马老师听我念了两分钟,说:“对,就这样,你这个稳拿奖。”
那篇文章我已不记得是什么了,念了两遍热身,有人匆匆来找马老师,说学校领导在开会,马老师叮嘱我好好念,自己录音,我乖乖答应,但已经有了别的想法。
看到马老师走了,他们家人也都走了,我坐在饭桌边,开始读。读了几句,就把火柴盒掏出来看了看。
那些蚕卵里面的小黑点越来越大,书上说,那比针尖还小的黑点是蚕的眼睛,就像毛鸡蛋里面,小鸡的胚胎上的黑点也就是鸡眼一样。
我将火柴盒拿到录音机旁边,我记得看科普书里讲,人造磁场能影响生物,而录音机里有一块或两块大磁铁,就藏在大喇叭后面。
我刚端过去,那些芝麻大的蚕卵里,一颗颗黑点齐刷刷地指向喇叭,就如磁铁吸引纸上的铁屑一般。
我试着换了几个方向,那些黑点始终如一,无意间我碰到桌子上的碗里的不锈钢汤勺,勺柄在瓷碗上发出叮铃脆响,那些小黑点集体一震,仿佛被晴天里一个霹雳吓懵了,过了片刻才缓过来,我又试了一下,果然那脆响会让它们一震一震的,正玩得高兴,从窗户看到马老师远远地走回来了,我赶紧收起火柴盒,继续念稿子。
下午两节课后有半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今天是星期六,摊着大扫除,而我厌恶劳动,况且,还有我和傲雪的节目呢。
我赶到“播音室”,其实那只是在校长办公室辟出来的一小块空间,堆砌了一堆黑色的播音机器,现在想来,大概是功放之类,还有一个裹着红布的麦克风。
傲雪已经在那里了。
我们打开电源,转动旋钮,红色和绿色的小灯在黝黑的大机器上闪烁,我们念:
“红领巾广播电台——”
“现在开始广播——”
晚饭后,我又把火柴盒拿出来看,愣了一下。
它们孵化了吧?
有一半的蚕卵已经破了,我细细地瞧着,找到发丝似的小蚕,在盒子底部边缘蠕动,我赶紧拿出桑叶,切成小细条放进去,那些小蚕好像有鼻子似的,蠕动着往桑叶条爬,我暗暗给它们加油,不久便看到它们开始吃起来了,只不过还不像劳动课本上说的,能听到沙沙的啮咬声。
妈妈给我一个大纸盒子,我把火柴盒放进去,又切了一些桑叶放进大纸盒,就盖上它了。
夜里,我突然醒了。
窗外好像传来细雨声,沙沙,沙沙……
我摸黑下了床,打开台灯,那沙沙声忽然停下,我又关了灯,它才响起来。
循着声源,并不是窗外的,而是窗台上的纸盒。
我忍不住又打开灯,盒子里静悄悄的,我抽开一看,桑叶条差不多被吃光了,原本细小的蚕,已经长到圆珠笔芯那么粗了,我赶紧又丢了几片桑叶,看样子都不用切了,那些蚕昂起头,黑黑的眼睛盯着我看了片刻,大概觉得我不是威胁,就爬到桑叶上,沙沙地啃起来。
我就看着它们吃,吃完一片放一片,不知不觉竟睡着了。
我又央求孟同学再给我弄点桑叶来。
她说,非得我找来的桑叶吗?我说是啊,我找了别的桑叶,它们不吃,就吃你带来的。
孟同学有些吃醋,不过还是去偷了他们家对头的桑叶,这次偷了一大包,我觉得差不多够吃到蚕宝宝长大吐丝了。
不料,才三天,那些蚕宝宝就把一大包桑叶吃掉了大半,我心慌了,又找孟同学,正好傲雪路过,我像是被勾了魂一样盯着她,再回过神来,孟同学没好气的说:“你自己去偷吧,我给你说在哪儿,我是不想去了!”
她看我呆愣愣的,不明所以,叹口气又说:“算了,我还是带你去吧,那地方不好找,而且,还要守规矩。”
“什么规矩?”
“黑獐村的规矩。”
去黑獐村的路途很远,也许是那时年纪小,又是没有走过的路,所以会觉得格外远吧,二十多年后我在Google地图上查了一下距离,大概也就十里路。
我们五点半放学,春天里白天短,才走了一半路,已经到了夜摸黑,我们出了柳镇,路边是熟悉而稀疏的大柳树,刷着齐肩高的白灰,偶尔有一两只夜魔虎掠过,大概还没睡醒,飞得歪歪斜斜。
“大河,你喜欢傲雪吧。”孟同学说。
我的脸一下子烫了起来,还好日光已经没了,孟同学也看不出我脸红吧?
“是吧?”她轻声笑着,“傲雪长得那么好看,你喜欢她也正常,你也长得好看啊。”
我很不好意思,就问她:“黑獐村的规矩是什么?”
孟同学没有直接回答,给我讲了个故事。
明朝万历年间,当时黑獐村还不叫这个名字,叫孟李乡,姓孟的和姓李的最多。
民间流言,万历帝找到了一位西洋道士,足足花了十年修了一条通天大道,那条道一直通向天宫,万历帝不坐朝许多年,就一直在大道上住着。
然而文武百官还是要开会,油盐酱醋也还是要吃,往常也就罢了,万历三十年,县里收税的要征用蚕丝,说通天大道需要蚕丝,用来吊住石板——老百姓并不相信蚕丝能吊住石板,可还是得交,而这一带本就不是养蚕的呀,养蚕都在南方温暖的地方。
那县令却说,不是养蚕的,为何此地桑树甚多?
俗话说“前不栽桑,后不栽柳,当院不栽鬼拍手。”那些桑树本来只是野生成林,哪有人家真去在意。不过既然要养蚕缴丝,人们就开始用这些桑树叶子来养蚕。本来第一年收成还行,那些桑树枝叶浓密,养得蚕宝宝肥嫩无比,第二年开始,却总是没有嫩叶子了,不知是被什么动物偷吃,结果那些蚕吃都吃不饱,别说吐丝结茧了。交不上足量的蚕丝,也不知多少人被罚没了家产,砍了头,但勉强结出来的蚕丝还是不行,今年春天再交不出上等货,连这三五户人家也逃不掉。
这一天,孟家的祖上一个当家的亲自盯着桑林,他提前一天就披了蓑衣躺在草丛里,足足熬到半夜,迷糊中听见有什么野兽嗷嗷的叫,他起身蹑手蹑脚靠近,只见林中月光下,一匹黑黝黝的小兽正从桑树上跳下来,嘴里含了一大捧桑叶。
这位祖先大喊一声,手里的梭镖就先甩了出去,一下子捆住那只兽,抓过来一看,是只浑身油亮黑毛的獐子。
“你知道獐子长什么样?”孟同学忽然问我。
“不知道。”我脑中只有“獐头鼠目”这个词,“大概像老鼠?”
“獐子长得像鹿,不过没那么好看就是了,没有花。”
孟家人把獐子捆好,磨刀烧水,要宰了它,那獐子也知道自己死期将至,竟呜咽流泪,忽然有人说:“獐子一窝得十几个,宰了这个还会有来的。”
怎么办呢?那聪明人说:“将它放了,我们跟着它摸到老窝,一窝端了。”
众人纷纷叫好,就把獐子松了绳,那獐子却站着不走,只呜呜的叫,真是奇怪。
碰巧,村里有个进京赶考借宿的书生,那书生也来看热闹,忽然说:“这獐子是想求好心人咧。”
人群里有人问:“你还听得懂兽语来?你是徐文长?”
书生一拱手:“不敢不敢,青藤老人能闻鸟语,我只粗通兽言。这獐子知道自己回去会害死一家,所以在求要么杀了它,要么有个善人发愿不杀它家人,就带谁去——它家里有灾要求助咧。”
孟家祖先说他愿意去看看,獐子前腿一跪,磕了三个头,众人不由得也吓了一跳,纷纷说这是有灵性的了,不能轻易杀。
獐子带着孟家祖先和书生还有李家的两个男人一路走去,过了一条小河,在三棵大树间找到獐子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獐子是母的,窝里躺着的公獐子已经死去多时,看样子是被野狼咬了,重伤不治,拼命逃回窝里后就死了,此时正是春末夏初,公獐子身上爬满了苍蝇,白骨腐肉,惨不忍睹,更惨的是,窝里还有几只小獐子,不知怎么伤口也感染了,上面还爬满了蛆虫。
那母獐子嗷嗷哭泣,把桑叶嚼碎了吐出来,敷在小獐子身上,书生看到说:“本草有言:桑叶苦寒,有小毒,桑叶绞汁可收痈口,去火毒,再者,獐子本来也爱吃桑叶……原以为是个兽贼,却也是良母。”
众人问该怎么办,书生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依我就先帮帮这畜生吧,权当积德。再说就是现在打死这一窝,你们的蚕丝也来不及交了。”
孟家祖先并不反对,李家的两兄弟出了个主意,听说土法里用蚕吃腐肉的,能清创愈合,李家兄弟却不愿意用本家的蚕,说是正当要结茧了,惊扰不得。
孟家就把自家的蚕运过来,倒在那些小獐子身上,又把死去的公獐子拖出来,当着母獐子的面挖个兽坟埋了,那母獐子长跪叩头。
小獐子身上敷满了桑叶碎渣,蚕宝宝爬上去就不断舐食,如此反复了两日,那些小獐子的伤口竟一一愈合了,而这一日,县里的公差也来催缴,孟家交不出来,李家却因为没有出蚕救獐子,刚好结了茧。
公差把枷锁铁链一套,就要把孟家祖先带走,刚到村口,就见一只黑獐子人立路上,抱爪作揖。
公差是吃横饭的,一脚将獐子踢了个趔趄,那獐子翻身爬起来,向桑林中跑去,另一个公差一拍大腿,道:“哥哥,咱们得发笔小财!这獐子是母的,必有小獐子,小獐子有什么?獐宝呀!”
獐宝是獐子幼崽胃里沉积的奶块结垢,虽然比不上牛黄狗宝那么知名,但也算是可以发笔小财。这两人将孟家祖先锁在就近的桑树上,便跟着母獐子钻进林子里寻窝。
这时我和孟同学已经走到黑獐村外了,远远看去,村子像一块扁平的黑砖压在大地上,除了一盏村口的昏黄路灯,就是家家户户阴暗的烛光,可能又停电了吧,黑獐不比我后来搬去的固城,固城挨着煤矿,夜夜灯火通明。
“后来呢?”我咽了口唾沫,晚饭点儿要过了,我还没吃东西。
“后来,他们找到了。”
他们在三棵树下找到了那窝小獐子,当下如狼似虎,将这些小的一顿乱棒,打得奄奄一息,用麻袋装了再返回路上,孟家祖先叹了口气,说他们要遭天谴,那两个公差喜笑颜开,不经意间被孟家祖先挣脱了镣铐,公差大骂,说你敢跑就抓你八十岁老娘。
孟家祖先一时急怒,枷锁横打,扫倒一个,另一个见状拔出钢刀,斜刺里冲出母獐子,将拔刀的一时撞倒,后脑磕在石块上,登时不行了。
孟家祖先返过醒来,手足冰冷,心想这下要满门抄斩了,却见母獐子跳到公差身上,四蹄乱踩,连那几个小獐子也勉力撕扯,把两个人弄得一片狼藉。
后来县里来了仵作,报明系野兽所为,现场还落下一只死去的小獐子尸体,县令也只好作罢。
“孟家的就是你们家了,那李家又为什么得罪了你们?”我忍不住问。
孟同学哼了一声:“母獐子虽然有灵性,可没到成精的地步,后来还是死了,它死了以后,被埋在李家的桑林地里,那片桑林就长得特别好。”
她伸手指指前方:“喏,就是那片。”
我们已经走到了林地,孟同学告诉我两家人桑林地界,中间有一排小土包,据说是獐子坟——那窝獐子的子孙后代一直伴随村子存在,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很少见到了。
我书包里有手电和粗布口袋,掏出来准备好,孟同学帮我把风,我便深入桑林去摘叶子。
乡下的夜晚,总有些奇怪的虫兽叫声,我虽然是接受了马克思唯物主义教育的一代,但因为经历了气功潮,还练过特异功能,所以格外敏感,总觉得林子深处有什么在盯着我看……很多双眼睛。
那时我身上还带着蚕宝宝呢,不过火柴盒已经装不下它们了,现在用的是一个回力鞋的鞋盒子,放在我书包里。
我总想先让饿了半天的蚕宝宝吃一顿,就趁着手电光,摘了一把桑叶,跟北方的高大桑树不同,这里的桑树长得比较矮,只有一米多不到两米高,我摘了两把塞进鞋盒子,顿时听到细碎的刷刷声,那些蚕宝宝正在大嚼特嚼吧……忽然有什么东西从耳边嗖一声擦过。
我吓了一跳,心想是夜魔虎么,夜魔虎也喜欢吃蚕宝宝的,无怨得是老鼠变的。于是我用手电打了一圈,没看见夜魔虎,倒是看见一只苍蝇。
只是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苍蝇。
那苍蝇足有成年人拳头大小,就趴在我面前一米外的一棵桑树干上,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只见它两片淡绿透明的翅膀,硕大如鸡蛋的下腹部,铅笔芯粗的两条后腿正翘起来,慢条斯理地刷洗着后翅,我打过很多只苍蝇,对这个动作熟悉得很。
忽然那苍蝇转过头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一直觉得林子里有很多双眼睛盯着我——那是噩梦般的一个苍蝇头,两个大鱼泡似的复眼,正反射着我的手电光,晶莹如恶魔。
我吓了一跳,手里紧紧抓着书包,此刻桑林里除了蚕宝宝细碎的啃咬桑叶声,四下里一片寂静。
隐隐约约,外面传来孟同学的叫声,好像是叫我名字,但桑林里听不清楚,我并没有走太远啊。
我摸摸书包,才塞满一半,就先不管那只大苍蝇,赶紧捋叶子。
忽然桑林里起了风。
那风不知道从哪儿吹来的,但紧接着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伴随着风的,还有嗡嗡的振翅声,我转身用手电照过去,看见了一堵墙。
这堵墙上闪烁着百万颗细小的红色眼睛,是苍蝇的复眼,如同璀璨的碎钻一般,但我只觉头皮发麻,尖叫着想跑却两腿发软,那是几百只拳头大的苍蝇群啊,这堵墙嗡嗡叫着逼近,轰一声散裂,苍蝇们铺满了我全身。
“大河!”孟同学的叫声总算近在咫尺了,我不敢张口,怕苍蝇爬进我嘴里,只拼命挥舞手里的手电筒。
在手电的光柱中,我看到孟同学并不急着过来扑打苍蝇,而是抄了一根尖头木棍,在地上掘土。
我知道苍蝇是没有牙齿的,它们嘴上是个吸盘,一伸一缩小喇叭似的去舔食物,但这么大的苍蝇还是吸盘么?不及我多揣测,孟同学已经掘开了土堆,那土堆里忽然爬出几个白色的小动物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