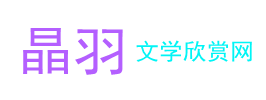关于回族信仰的美文
来源:宗融艺文馆
荐读回族宴席曲曾经内里丰富,兼容并包。既有汉文化传说和历史故事,又流露出回族人孤独的底色,包含了回族打开胸怀学习一切的态度,也透露着他们时时谨防被异化的文化宿命。闪着朴素光辉的宴席曲,深藏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然而在回族人民漫漫修远的求索之路上,在环境的巨变之下,宴席曲渐渐退场。“窥见了历史的翻页,究竟是一种收获,还是一种痛苦?”本期刊发青海回族作家马有福的文章,我们渴盼以孤单的微力唤起无数回回儿女对远去文化的礼敬。对于在历史长河中没有文学作品相伴的回族来说,宴席曲就是他们的文学。那黄河决堤般淤积在心中的块垒就通过宴席曲得到了充分的宣泄。 渐行渐远的背影
马有福|文
一
每每想起回族宴席曲,我就想到消失已久的清油灯。在记忆的地平线上,它们一度摇曳在乡村的黄泥小屋里,温暖了人心,照亮了贫苦,驱走了回族先民们与生俱来的千年孤独。
想宴席曲诞生时,回族先民们刚刚问居中华。那时,汉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处鼎盛之势。“知识哪怕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先知穆罕默德的一句告诫,就使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成吉思汗西征时的俘虏),怀着对中国的向往,怀着吸收一切、消化一切的大胸怀,散居在中华各个角落。不久,在入乡随俗的过程中,未经踌躇,他们很快学会了汉语,也感知到了唐诗、宋词等代表了汉文化的最高水平,但对于刚刚适应汉语和汉文化语境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毕竟是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大多数人还达不到像五代的李珣等人那样的修炼和造诣。这使得他们有一种被排除在外的隐隐的忧伤。就是这一丝忧伤,奠定了回族文化命运中就是到了今天想甩也甩不掉的孤独的底色。
宴席曲就诞生在他们颇觉得意,也觉失落和孤独的元代。这,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推测。
我始终这样认定。几十年来也一直通过读书和聊天求证着,到今天也没有看到过言之凿凿的结论来否定自己。我常想,元代是孕育和诞生了回族的时代,那时,元曲比成吉思汗的铁蹄还要厉害。它,像一股风,一经刮起,就长久不息,这使它比今天的流行歌曲还要普遍地走向民间。与唐诗宋词相比,它更亲切,更民间,更妇孺皆知,也因而更大众化。它的平民性、普及性使它培养了一大批歌手,既有文人也有文盲,拉近了文人和民间的距离。在这几近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元曲的氛围中,回族人受到了熏陶,灵机一动,就创造出了宴席曲这样一种专在婚礼场合表演的音乐形式。在这样的音乐形式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至今,每听宴席曲,我犹隐隐感觉到先民的心声。那种身处沙漠而不惧一切、扫荡一切的凛厉,那种冰消雪融、风卷残云的从容与豪放,还有那一丝人生苦短、生老病死的忧伤。它们搅和在一起,依旧清晰地表达着先民的心声。
自此,回族宴席曲陪伴着回族人打发光阴,生儿育女,妆点生活,直至几近消失。
我第一次接触宴席曲时,尚不到七岁。那时,乡村一片凋敝。我的父母为一日三餐而不分昼夜地干活。他们是生产队的壮劳力,一本经常揣在衣袋里、被尘土和汗腥浸透的皱巴巴的《劳动手册》证明着他们的价值,也控制着他们的人身。日子过得极其艰难。比这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人届中年的他们等不及我去接他们的班,而姐姐的出嫁又是迫在眉睫的。那时,农民们在现实面前形成的铁打不动的逻辑是:待我的父母失去劳动力,随之而来的便是没有口粮保证的凄惨晚年。处在这样的思绪里久了,人也就短了精神。正在这时,按照村里的传统,我家给姐姐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在女婿入赘的日子里,我家变成了全村的中心。白天摆席待客,夜晚唱曲相庆。我就这样感受到了宴席曲带给我家的尊容。
在天将黄昏的时刻,约二十多个曲把式相约来到了我家。他们满面笑容,相让着进门。父亲说着色俩目热情地迎出去。平时,他们跟我的父亲一样都是灰头土脸的村民,但在这一晚,他们却意外地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尊贵。我家各个屋子里都点了青油灯,炕上坐满了亲戚,地上站满了左邻右舍,房屋内俨然人头攒动,加之,我家那时竟连一条凳子也没有,父亲就把他们让到柜上,让他们垮在柜上演唱。在他们的身后,两个瓶子里,是父亲专门给他们买来的一斤白砂糖,一斤红砂糖。那木柜矮小破旧,毫不起眼,前几年我在清理父母和儿子遗物时,为免得它们一再地让我看得伤心,就砸成劈柴烧了。但在那时,却是我家的最高堂,也是最大的脸面。它摆在堂屋进门的泥墙下面,凡我家值钱的没有泡花的花瓶和亲戚们拿来的礼品都是放在那里的。外人进门,第一眼落处就是这一对木柜。木柜上面的东西、以及东西上面的土墙上糊上的报纸或一张画,就是一个庄户人家所有的脸面。可见,我父亲曾经为了招待曲把式而费了多大的心思。看着那一白、一红装着砂糖的瓶子,我就觉得我家阔绰得不知到了什么程度。
我家例行先给他们吃酸菜粉条、糖肉包等待客的上好晚饭。随后,烧熬茶,派堂兄给他们续水。白、红糖由他们自己掌握。这在当时的乡村里是多大的奢侈和享受啊!说穿了,曲把式唱一夜曲子,也就只有这么一点可怜的报酬,或者说是待遇。
曲子的内容,我当时是一点儿也没有听懂。我所记得的只是我们家那一夜热闹非凡,盏盏青油灯下人影绰绰,致使平时安居在我家屋檐下的十几只鸽子也飞来飞去地打下了不少梁吊灰。后来,回忆起这一夜热闹时,母亲说,那晚,她搓下的二十多根棉花灯捻和炸馓子剩下的几斤青油都被用得差不多了。他们一派知足。在村民面前,他们终于体面了。
一夜宴席曲,一村开心事,我们没有被村庄抛弃。
对于这一切,我始终没有清晰的记忆,也始终没有遗忘过。所以,这一夜(包括宴席曲)于我,始终像一盏摇曳在乡村冬夜里的青油灯,既恍恍惚惚,又温馨无比。借着这样的感觉,后来,我才有了对宴席曲探索的兴趣。
二
说来有点意思,我学习、探索宴席曲的机会却是在远离了家乡、远离了正常社会生活的古金场。这是一个没有女人、没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规矩的纯男人世界,我把它视之为社会的真空,也视之为我的大学。
在金场里,每天一起来,就是铁锨、砂尖的撞击声。吃的是开水兑面的三餐,睡的是石板拼凑的地铺。人的生活简单至极,也孤独之极。这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大多变成了一张白纸。但越是这样,金客们的思想就越丰沛。这是一个可以孕育哲学家的环境。于是,这些大多目不识丁的农民们在白天总有唱不完的花儿。
架子车拉下的肩头痛,
铁锨把抓下的手疼。
大白天想你着肝化痛,
每晚夕里想你着心疼。
他们想家,想家乡的一切,也想曾经失去的生活。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聊起了回族宴席曲,也同时在休息的时候唱起了宴席曲。让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与我一块儿干活的老人就是一个曲把式。他会各种各样的曲词,曾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青春的他,对人间的各种苦难的理解有着不同于别人的深刻。
他说:“宴席曲说是宴席曲,实则是个苦曲,心中没有泪水的人唱不出感觉。”在整个宴席曲中,开场的恭喜曲和夹杂在中间的打莲花(与戏曲中的插科打诨、打搅儿、打王变)只是为了活跃气氛,而宴席曲的味道全在它的叙事曲中。
就这样,我开始了对回族宴席曲的补习,把金场变成了课堂。
曲把式老人首先告诉我,花儿是情歌,花儿只适合于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倾诉,是单对单的,因而,有很多在众人前不能开口的尴尬。有一句花儿是这样唱的:“到了庄子里你别唱,你唱时老汉们骂哩!”你想想,两口儿间的私密话、悄悄话能够被说破而让众人听吗?这样,说的人没脸,听的人害羞,所以,花儿就是花儿,不能与宴席曲相比。
在跟老人学习的过程中,我还了解到,花儿是野曲,只适合在田野里传唱,一般是唱给单个人的情歌,就像书信,有固定的承接者,它更擅长于抒情。而宴席曲是家曲,它是在黄泥小屋的炕头上唱的,听众可以是父母儿女,不需要互动,它倒像一部部文学作品,更擅长于叙事。
哪一个教授的研究生,能够这样不厌其烦地向老师请教呢?在我们聊天中,兴之所至,老人就会停下手中的忙务,给我来一段花儿或宴席曲,在比较中,让我学到了在书斋中永远也学不到的知识,也使我枯燥的金场岁月充满了情趣。
“抬起嘛头儿瞧,抬起嘛头儿瞧,我把我的穷东家表一表。”就从这里起行,在曲把式老人满含沧桑的声音里,我一头沉进宴席曲。我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穷人疼爱穷人的朴素;穷人日子窘迫,衣着褴褛,形容枯槁,他们被淹没在穷日子里,一年到头没有几天从容和宽裕。他们一辈子的愿望,无非是打一个土夯的庄廓,盖几间藏身的茅屋,然后,东挪西借地给儿子娶媳妇、打发姑娘,再然后哄孙子、干家务,直至把后辈带到自己曾经的人生轨道。简单而又艰辛,但他们认命、安然。于是,曲把式们在儿女婚姻的晚上,既是帮衬,又是助兴地例行要把东家夸一夸。这使平日里将凑着过日子的东家一下子成为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心中的灯盏,既明亮又温暖,自尊一下子被显示出来了。这是多有意思的来自乡邻们的礼物啊!
在东家之后,他们紧接着夸媒人、新郎、新娘、伴郎、伴娘,以及嫁妆和他们自己:
抓灯盏的阿哥你往前抓
我把曲把式阿哥们夸一夸
歪戴的帽子索连线
斜穿的皮袄肩头上担
大包的带子腰里缠
鸡腿的套裤一裹沿
绣花的裤带大腿上担
丝布的袜子大脚上穿
好像朝里的一个官
从以上自夸的词中可以看出,曲把式们犹如今天的各路演唱明星,他们自有他们的风流与潇洒。其实,这也是他们对于自己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生活中的他们,除了那一腔歌声,再也不会有更加富裕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唱起来,才会如泣如诉、义无反顾。有研究者认为,回族宴席曲有着蒙古长调的委婉,也有黄河一泄千里的长驱直入。我认为,这是比较接近实质的评价。因为,回族人心比天高,他们始终有一腔似火的追求理想的热情,然而,残酷的现实和修炼不够,往往让他们的理想得不到实现。这是产生悲剧的基本缘由。一切文学作品,几乎都是悲剧。对于在历史长河中没有文学作品相伴的回族来说,宴席曲就是他们的文学。那黄河决堤般淤积在心中的块垒就通过宴席曲得到了充分的宣泄。
金场体力劳动的强度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使我疲惫不堪。然而,与曲把式老人在一起干活,一起品味宴席曲,我犹觉在享受回族文学的盛宴。在沙石相撞的天籁之境,在山溪喧哗的金槽之岸,老人一曲曲歌声,把我带到了农家的炕头,带到了遥远的边关,带到了征夫思妇的泪岸,也带到了一个个拉扯儿女艰难度日的老农的心中。
“好男儿要去个打围场,好女儿要去个宴席场。”宴席场是女人们展示和学习的好机会。在封建社会,许多女人终生的生活舞台就是自己的家庭,她们对于外界社会的了解很有限,这使得她们把宴席场看得很庄重,所以,平时哪怕是节衣缩食,在宴席场也尽量地穿的体体面面、光光鲜鲜。赴宴的人多,但东家的炕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曲把式们的一夜曲子,使来客想睡都睡不成,免了东家不少尴尬。同时,也让客人们听了一夜曲子。这样的好事,谁不喜欢?
听着、聊着,我和曲把式老人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地上,猜测和判断着宴席曲的功能,忘了紧拿着铁锨而失去伸展功能的僵硬的十指。有一天,天降大雨,山溪暴涨,干不成活了。帐篷里,在雨点噼哩啪啦的伴奏声中,曲把式老人手端着他的既是茶杯又是饭盒的铁缸子唱了起来。唱着唱着,他自己的眼睛湿润了,几位后生转过脸去也在揩鼻涕。他说,这眼泪是由不得人的,在宴席场,女人们听着听着,就先是用盖头或纱巾的一角偷偷地拭眼泪,听到动情处,就抽泣成一片,让我们的歌声变成了河流,水淋淋的,谁都不好受。
《祁太福》、《不耐宿》、《方四娘》、《哭五更》……我知道了许多曲子。神奇的是这些曲子,吸收了很多汉文化传说和历史故事,如孟姜女、诸葛亮、穆桂英等,但在裁取的过程中又融入了回族的情绪。这之中,几乎包含了回族既打开胸怀学习一切,也时时谨防着被异化的文化宿命。
出门不唱《祁太福》,在家时不唱《不耐宿》。这是有品的曲把式们的坚守。因为,他们认为,唱曲最终的目的是给人长精神,而一支曲子让人心灰意冷、失去了进取心,那是糟蹋曲子。
“灯不灭,心不歇。”这是《不耐宿》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词。由此,我推断:在这些穷人把式的心目中,那颗娱人自娱的心,始终如东家的青油灯,高高悬挂在乡村的夜空,伴着一缕从不推卸的责任。
三
怀着对宴席曲的喜爱,我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便着手收集有关宴席曲的资料,想彻底搞清楚它。然而,在我的活动半径里,这样的资料依旧凤毛麟角。除了甘肃临夏州群艺馆编印于1984年的《回族宴席曲》,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87年的《青海回族宴席曲》之外,直至2007年在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的强力推动下,中国文史出版社出了一本具有门源特色的《婚宴喜乐:宴席曲》。当然了,还有不少隔靴搔痒的有关宴席曲的论文,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在读着这些书籍和资料的过程中,会遭逢眼前为之一亮的句子,也常常少不了会心一笑的场景。在这些看似土得掉渣的词曲中,每每透露着整个回族人的身世命运。他们远征的沧桑、他们入籍的身份、他们的异乡恋歌、他们的春闺怨歌、他们的英雄情结、他们的悲苦境遇、他们的相濡以沫等汇聚成了他们自己都几乎感觉不到的千年孤独。
在乡下任教的日子,为了增加课堂气氛,我曾经试着将古诗《陌上桑》与宴席曲《祁太福》就表现手法做了对比教学。学生认为,宴席曲表现天黑的一段与古诗里各色人等见秦罗敷的手法几乎如出一辙,他们都曾背得滚瓜烂熟。在教《孔雀东南飞》的日子里,我觉得宴席曲《方四娘》可以与之比美,就把词抄到黑板。想找一个曲把式,几经周折,终未找成。后来,我时时打听着,看哪儿有没有表演宴席曲的婚礼,想去感受一番。但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一致的:早已不唱了。
套用张承志散文中的一句话:一页翻过!现实无情地抛弃了宴席曲。宴席曲自身也变成了一个无人招领的弃妇。
就这样,让一个流传了很久的民间艺术曲目从我们眼前消失。多少人于心不忍。前几年,我几经奔波,选中了家乡的一个年近七十岁的曲把式老人,想以他为主人公做一个纪录片。要上电视了,老人自然很高兴,也约好了几个老搭档。但为了找到一个接受演唱的婚礼,我跑了很多路,协调很不顺利。村里谁家都不唱了,主人家都担心大家群起而攻,孤立一家。拍摄当晚,老人的儿子坚决不让他出门,倒不是担心他的身体,而是名声。在儿子一代的观念里,唱曲是严重的为老不尊。
在拍摄现场,主人家的院子里,灯火辉煌,鞭炮连连,一派喜庆。录音机放在房门口,音量超高,小青年们沉浸在旋律中,手舞足蹈。屋子的客厅里,一大帮亲戚在关注着世界杯,不时鼓掌。喜庆倒是喜庆,但我觉得喜庆得有点七零八落,不完整。为了现场效果,在主人家的劝说下,院子才恢复了一点宁静和单纯。宴席曲开场了,所有人都围过来,觉得很新奇。但不等一曲唱罢,很多人对我们摄像机寻像器的好奇胜过了宴席曲。尽管也有人在听,但从他们的眼神判断,他们一点儿也没有进入的感觉。过了不久,许多人打着哈欠转身走人。
唉,七八年开始的经济关,
向钱看,
穷光阴催老了那英俊的少年;
唉,现在的年轻人他靠了边,
挣不上钱,
新媳妇尽爱的是老汉。
难道这就是注解?在与曲把式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几乎不加怀疑地把宴席曲的命运归结为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金钱无孔不入地统治了所有人,人与人之间最牢靠的关系也只剩下了钱。而宴席曲最注重的是一个村庄的村民对办婚事主人的疼爱与尊重,它以集体礼的形式存在了很久。而今天,人都变实惠了,变浅近了,人们的婚丧嫁娶简化成了一笔笔交易。以前,村庄有喜是大家的喜,村庄有难是大家的难。凡遇上房泥、打碾、送葬等大事时,全村都停止自己工作而围到了一家,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水帮船、船帮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而今天,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之间是竞争的对手。在这样的时刻,宴席曲的退场是必然的。看着它隐去的背影,我们除了叹息,再也无可奈何。虽然,经过一些仁人志士的努力,回族宴席曲被推上了形形色色的舞台,也被列为全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它已经深深地被打上了吸引眼球、推动旅游的烙印,离人心、离它诞生的土壤,依旧有一段距离。我认为,回族宴席曲的生命舞台,就像这世界上所有艺术的生命一样,永远在人心。
(原载《回族文学》2009年第1期、《天涯》2010年第6期)
作 者简 介
马有福,1965年生于青海大通,媒体人,著有《大道至亲》等六部作品,现居青海西宁。
表述自我END关怀他者
主编 | 泊石
本期编辑 | 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