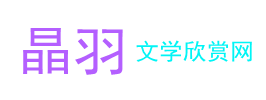关于大学同学情的美文
青年时代的人生,是打起背包就出发的仓促远足。
外面的世界,想象中是精彩和美丽的。可历过风霜雨雪,你才知晓每一步都有深有浅,每一程都有舒心烦恼相陪伴,每一点启迪和开悟,都离不开别人的点拨和帮助。 也是走过来了,你才体会到在外面生活交接,也有“兄弟姐妹”般的亲切可心。
友情的暖心,也让你的满腔激情得以恒温不降,让你的步履如踏春风般写意欣然。 像许多人一样,我年轻的出发,也是没有思想准备就上路了。
那一年,大学恢复招生,经过自我报名,单位推荐,文化考试,我被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了。
正好,本工作单位市委报道组的师长贺宛男,也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她给我介绍说,复旦大学是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新闻系在全国的大学里又是独一无二的(据说当时北京大学只有新闻专业没有系)。而复旦大学的校长陈望道,又是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共产党宣言》就是他最早翻译成中文的。她说,“你有幸上复旦,以后我们就是校友啦。”
年轻遇幸事,犹如心里灌了蜜,怎能不快乐!
父母得知我就去大都市上海读大学,迅速决定杀了一头猪,卖得120块钱,全部交给我。他们说,上课要掌握时间,到了那里,你去买一块上海手表吧(可后来,上海手表凭票供应,一直买不到,钱,也只好带回来了)。
大姐给我一张毯子,二姐给我买回一斤毛线打了一件毛线衣。带上一张薄薄的棉被和一些简单的日用品,也带着父母的欣慰与叮咛,我,搭上了南宁开往上海的列车。
学校是9月1日开学,我和广西同系的同学黄仕业,还有中文系的刑志萍,国际政治系的蒙杰强于8月30日同车到达上海。
当天下车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吧,车站里灯光朦胧的站台上,有许多学校举着迎接新生的牌子。一路看过去,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学院,上海化工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
大家在努力搜寻“复旦大学”时,不远处有同学招呼了,“复旦大学的同学到这里来集合,我们一起回学校。”
“有车接我们去学校,不用担心在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里乱闯了。”心里一阵暗喜。 上了校车,我开始一路注视着陌生的街景。高楼、霓虹灯、立交桥一一在车窗快速闪过,街灯一盏接一盏向远方延伸,走走停停过了无数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也没有到学校。
“学校距离市区还是很远的哦。”看到路过“上海外国语学院”,以为学校就要到了,可车子还要走上好一段时间的路。
车子快速的开在去学校的路上,飕飕冷风贯窗而入,这时我第一感觉,上海的气候与我们家乡差别很大。来时,我们是穿着单薄衬衣上车的,可到了这里,气温倏然低了很多,一路上冷得我直发抖。
进入新闻系学生宿舍6号楼,是时已经11点多了。在楼下的第一个房间里,两位高年级的同学和一位师傅、一位老师接待了我们。
老师高瘦斯文,戴着一副眼镜。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周老师,是你们的班主任。以后常和你们在一起啦。”
他问我们行李到了没有,黄仕业同学应声说∶“行李托运了,一两天才到。”
周老师转过身,跟一个叫小吕师傅的说,“看来要给他们去借被子才行了。”
“好的,我去办理吧。”小李师傅转身就出去了。
当晚,睡在新闻系学生宿舍6号楼里,做着踏实的梦。这时,我觉得,还在初中时就梦想将来到大城市读大学的理想,终于梦想成真了。
第二天注册。来到学校统一注册的大厅,这里早已人头攒动,不少新生也是今天到来注册的。
大厅里开了许多窗口,每一个系负责一个窗口。我在一旁驻足,正睃寻新闻系的注册窗口时,一个娇小俏丽的女生打我身边走过,我看看她,她也看看我。她走到问询处,问工作人员说∶“请问新闻系注册在哪里?”
工作人员即告诉她说,是第五个窗口。
“哦,她也是新闻系的”。不用问,我注册也是与她同一个窗口了。
我站在她身后,只是耐心的等她办完自己的手续。拘谨的我,也不敢动问这个“同窗”的姓名。可正是这位“同窗”,在后来的三年学习与生活中,她给予我许多的帮助。
来自二十几个省区的同学都到齐了。周老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班务会,他在会上宣布全班成立临时党支部,同学分为四个小班,并宣读了临时支部委员人名,和各个小班的同学名单和班长姓名。我分在第四班上,章佩敏同学既是支部委员,也是四班班长。真是巧,她,正好就是我注册那天第一眼见过的那位“同窗”。
后来得知,章佩敏小小年纪,在原工作单位就是党员了,可见她工作很出色。
章佩敏性格活泼、开朗、爱笑,为人亲和、细致、贴心,是上海本地同学。
班上的上海同学较多,平时学习讨论,他们爱用上海话发言,章佩敏对他们说,“还是说普通话吧,好让我们外地的同学都能听得懂。”
后来,我们外地同学都爱捞几句上海话,这时,她又耐心的教我们说“阿拉”“勿嘞瑟”“嘛好咯”……
随着冬天的到来,天气日益寒冷,章佩敏看到我和黄仕业的被子比较单薄,也没有褥子垫底,她教我们买张棉胎回来,上面再铺一块被单就行了。她说∶“假如没有被单,就扯几尺布也可以的。”之后,她介绍我们到四川北路购买棉胎,并告诉具体怎么走,搭乘几路车,再转几路车,在什么商店可以买到。(我后来买回的那张薄薄的棉胎,一直保留到现在。)
在上海第一次过上一个温暖的冬天,我感受到了同学间相互关怀的暖心。
其实,这种浇灌心灵的暖流,也不止来自一处。
当年寒假,我们外地同学大都没有回家,春节就在学校里度过。上海同学刘海贵担心我们节日寂寞想家,他将我们邀请到家里,做了许多特色菜肴招待大家。
让我记忆尤深的,是那盘只有红瓜子大小的蛤蜊。在品尝这道菜时,怕大家说我是“土包子”,不敢问他们怎么吃法,我连蛤蜊壳壳,也咬碎吞到肚子里了。
第二年春季学期,我和同学们一起到崇明岛搞农村社会调查。那时春寒料峭,天气还很冷,我只带去一张薄被和那张垫底棉胎。到了驻地,发现床铺不是木板床而是铁丝网床,铺上被褥后,柔软的棉絮都从网孔里钻了出来,根本不能睡觉。宋德芳同学看出我一时的无奈与尴尬,他说∶“你没有褥子,我给你一张塑料薄膜吧,把它垫在底下再铺上棉絮就行了。”他还热心的过来帮我铺上。
得益于他那一张包裹铺盖用的塑料薄膜,这才解了我的一时之困。
可是,后来几个晚上,我觉得被窝特别的冷,晚上常常睡不着觉,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直到收队回校捲起铺盖时,发现垫底的棉絮居然可以拧得出水。原来,是体温化气,塑料薄膜散发不出而衍成积水了。
其实,那十几天,一直都是睡在水上,我也全然不觉。这,也算给了我一次扎实的生活经验了。
那年冬天,我们又到工厂搞企业调查。我和刘晓萍、陈华芳、魏文、谢罗、张国良等几位同学分在一个小组,下到一个纺织厂。那次寒潮袭来,气温很低。刘晓萍、陈华芳见我只穿一条单薄的裤子,于是对我说∶“小龙,你一条单裤过不了冬,去买回毛线,我们给你打一条毛线裤吧。有一斤二两就够了。”
于是,我按照她们的吩咐,买回了一斤二两黑色的便宜毛线。刘晓萍、陈华芳、魏文妍三位女同学利用空余时间,轮流编织。高干小姐谢罗不太熟练,但在她们三人织累了的时候,也拿起织针接着慢慢操作。不到一个礼拜,一条暖和的毛线裤,就穿在了我的身上。
同学情深的眼睛,在你生活上稍有失虑和不适,他们都会看得很清楚,并适时伸出援手以予相助。而对你一时的冲撞与冒犯,他们也没有往心里去,并很快就让情绪的不爽烟消云散。
在解放日报习习时,我与张国良分在编辑部农村组。一次,我和他接受了领导交待的一项采访任务,到松江某单位采写一篇内参稿件。采访后动笔写作时,我与他有些看法不一致。也许当时大家都年轻气盛,一时也调和不了。于是,我只好建议在稿子里注明谁要怎么写的内容。后来,主编采用了我的写法,稿子发出后,那天午休,在朦胧中,我听到张国良坐在我的邻床边,正反复读着我写的文字。
性情温和且年纪最小的张国良,没有记怀我的倔犟。他自始至终跟我掏心相交。一次星期六回家时,他邀我星期天去他家玩,并把自己家的地址线路画成交通图给我。遗憾的是后来没有去成。可他给我的那张线路图,我也一直珍藏了许久,直到搬家才处理掉。
人都说上海人小气,好计较,我没有这样觉得。因为如此宽怀的上海同学也不止一个张国良。与倪奇峰也有一段值得回忆的往事。
记得新生第一学期学军到部队,我与倪奇峰同一个小班的十几位同学,下到空军地勤某部。为把在军营里的各种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周老师分配我出任战地“黑板报”临时主编。
学着一本正经的样子,我认真的进行组稿、编辑、排版。收到倪奇峰投来的一首小诗,我看了,觉得稿件思路不太集中,便大笔一挥,进行了大改动,四句改动了三句。我以为,这样做他会佩服我的水平。可稿件一登上板报,他就对我很有意见。他不无埋怨的说,你怎么能这样大改我的作品的?
我蛮有理由的回答说∶“给你厘清了稿子思路,不是很好吗?”“要改,还得叫我改呀,你不是强加与人吗?”他很不开心的回答我。
这事,给周老师知道了。周老师找我谈话,他说∶“修改文章,要学会尊重别人,大改作者的东西,也要征得别人的同意才好。”这,也是周老师教给我做人的一番道理啊。
我知道自己确实做得不对,但后来也没有很好的跟倪奇峰道一声歉,可他也没有因此记怀我的不是。后来,倪奇峰和舒平,还成为我入党的两位介绍人。倪奇峰为人大度、宽厚、心无芥蒂,想来确令我惭愧。往日对他的缺失,现在,也只能在这里向他道一声迟来的“对不起”了。
岁月如流,往事如船,它载着光阴连同我们日渐进入晚年佳境。
如果说人生是美好的,那是因为有许多美好的回忆,让我们慢慢咀嚼。
美好的滋味,时时滋润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精神生活日益变得纯粹、高尚且更加快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