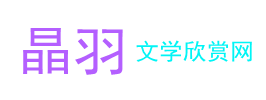关于安丘名胜的美文
点击“安丘发布”免费订阅我
编者按:春天,嫩芽初绽,鲜嫩鹅黄,如一条小溪清新明亮。到了夏天,植物往高处耸翠,向远处铺绿,恢弘成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本期,我们推出安丘作者写安丘夏天的一组随笔。这里面有温馨的回忆,也有现实的观照;有对安丘景致的浓笔重彩,也有生活其中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刻画。惟其如此,这样的夏天才波澜壮阔,它的壮阔来自它的容量。有夏夜的蝉鸣,也有小雨的滴答;有河流的潺潺,也有镰刀唰唰的割麦声。它既勾起回忆,也让你关注当下。让我们一起走进安丘的夏天吧,聆听夏夜鸣蝉的小提琴协奏曲,也聆听劳动者的步履应和着大河的节奏,走向夏天的深处。
夏夜蝉趣
刘文波
当第一声蝉鸣从树上流泻下来,真正的夏天就开始了。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芒种过后,麦子上了场,进了仓,就是蝉的幼虫出土的时候了。我们乡间管蝉的幼虫叫蝉猴儿,也叫知了鬼儿。
几声惊雷,一场透雨,就将地下沉睡的蝉猴儿惊醒了。当第一只勇敢的蝉猴儿化做具有金色羽翼的蝉,并唱出第一曲夏的抒情诗时,同类们也象受了感召似的,纷纷从地下急不可待跃跃欲试地钻出土层。而捉蝉猴儿就是我们童年的最大乐事了。
蝉猴儿是一种体态臃肿笨拙,身着厚厚的盔甲的小虫。一对车灯似的大眼睛,一双举重若轻的硕壮的前足,逢山开道,挖穴御敌。虽然其貌不扬但却威武矫健,不怒而威。蝉猴儿对光线非常敏感,所以它从不会在光天化日下钻出土层,而是在向晚的黄昏,先将洞口挖到接近地面的土层,只留一个小孔等待机会,伺机出洞。
所以寻蝉猴儿要在黄昏时分,将放饱的羊群赶回羊圈,菜篮子丢在门口,拿一把铲子,仨一群,俩一伙地到河滩的柳树棵子,杨树林子,葡萄藤前,葫芦架下寻蝉猴儿。寻蝉猴儿的工作需要耐心细致,不管大人孩子一个个弯腰弓背,慢挪步,细留神,不能放过一个细小的孔穴。没有经验的孩子连蚂蚁洞,蚯蚓窝也不放过,所过之处一片狼籍。而有经验的则只关心那些看似不规则的榆钱般大小的孔穴,轻轻一抠,去掉表层的薄薄的一层土便是拇指大小的蝉虫的洞穴了。找到的一声欢呼,其他人便聚拢过来,看到别人有所收获,于是更加仔细认真。待到太阳西下,光线模糊,地面再也看不清了,就要等到月上柳梢,借着月色来寻。或者背着大人偷偷地将家里的手电筒拿来照那业已钻出洞穴开始爬树的蝉猴儿了;而那时除了黑夜浇地看园,是轻易不用手电的,所以用了以后要偷偷地放回原处,但两节电池用不了几次就光线发暗,因此是免不了要挨揍的。于是就凭手感来摸,绕着树干从下到上摸一圈,运气好的一晚上摸个十来个,几十个不成问题。但有喜也有惊,有时回摸到一只毛茸茸的大肚蛾,踩到一只癞蛤蚂,惊出一身冷汗。而那荒郊野外,乱坟岗处是独不敢去的。大人也吓唬孩子说那里的蝉猴儿是吓人且附了阴气的,吃了也是要生病的,因此也从未去过。
等到攒上十天半月,檐下的腌渍蝉猴儿的小罐已数目可观了。即使兄妹几人合用一个器皿,每个人也是心中有数,赖不得的。腌透了,晾干了,然后在油锅里一烹,油亮金黄,令人垂涎欲滴,还未出锅就已按捺年不住,急不可待地从油锅里拈出一个先解解谗,尽管烫得连连吁气。或者将晾干的蝉猴儿直接放母亲摊完煎饼的鏊子窝里,用灰烬焙干,那也是别具一番风味的吃法。一家人一起美餐一顿,这时原先偷用电池的不光彩也就瑕不掩瑜了。
而这种会餐也只是开开荤,打打牙祭,断断舍不得将劳动成果自给自足了,而是要积攒着,等到下乡收蝉猴儿的小贩一声吆喝,尕小子,辣妹子就将舍不得吃的蝉猴儿用盆儿、碗儿、罐儿的倾将出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换成书包、本子、连环画了,因为那些精神食粮似乎比短暂的口腹之欲更长久,更能带来深层的愉悦。岁月的艰辛使那幼小的心灵早早懂得了这些。
而今那吵的令人烦躁的蝉鸣弱了许多,只在山冈荒岭还有一些疏落的声音。蝉鸣少了,夏意便显得单薄了许多。而酒桌上的油炸蝉猴儿的价格也日渐攀升,先前捉蝉猴儿是生活的逼迫,充满着生活的艰辛,而今看着吃够了鱼肉荤腥,生猛海鲜的食客,为了图个新鲜而在餐桌上的大快朵颐的吃相,我却难以下箸。
那时寻蝉猴儿可以说是苦涩生活的一部分,给艰辛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和希望。而今,对于那些少却了那种生活体验和经历的饕餮食客而言,它只是入酒的佳肴,佐餐的美味,又能吃出什么滋味呢?
蝉是一种微漠的昆虫,乡间只是以虫子相称,却也是天地之精气,日月之精华。上了学,读了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介绍蝉的文章以后,打内心里增添了一种敬佩。三年的黑暗中的苦工,一夏的阳光下的放歌,完成由地狱到天堂的飞升,这种生命难道不值得歌唱吗?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够听懂这发自肺腑的生命的声音呢?
蝉是弱小的,却是有用的。蝉蜕是中医的一剂方剂,疯干的蝉也可入药。小时侯,我就是用它治好了母亲的病。这也是我对蝉深怀的另一种情结。
所以我为能寻到一只蝉蜕而欣喜,找到一只刚出土的蝉猴儿我也会将它放到远远的树丛中,因为又有一只居高声远的蝉儿逃脱人口,我会为此高兴。
在唐诗中有“蝉噪林愈静”的诗句,赞赏环境的幽雅恬静。可是如果没有鸣蝉的高歌,又哪有静谧的诗的意境呢?放而言之,如果少却了鸟鸣、虫吟、蛙噪、虎啸,天地喑哑,阒静恐怖,生活其中的人类不会感到太孤单寂寞了么。
所以,唯愿人们能听懂这天籁般的声音,愿这世界少一些物欲的喧嚣,多一些纯真的鸣蝉的聒噪。
夏日小院
刘学刚
一条黄土路联结着206国道,使得宿舍与外界保持着短小又跳跃的距离。黄土路,纤细,淡定,植物叶脉一般,隐在了大片的绿色里。夏日,沿一溜阴凉走回去,就像是从喧嚣的现实回到静谧的内心。院落很大,空地也多,白杨树异常挺秀,看久了,眼睛会微微发疼。蚂蚱们在野草里沉着地恋爱,繁殖,也经常来宿舍串门,我一出现,就被认定是它们的亲戚。很多空地被开垦成菜园,大家一起挑水浇菜,拔草施肥,公共生活如同在讲台上的授课,明朗,透亮,通俗。
一排排砖瓦房,独门独院,过往的读书声凝固成砖石,自有一种端庄宁静的氛围。学校给的两间宿舍,切分四个单元,西墙一块黑板贯穿着客厅和偏房,走来走去,感觉是在课文的某些情节里,淡出淡入。满院子寻来碎砖头,铺就一条甬路,从大门口到屋门,梦乡的入口平坦,干净。小院很大,总不能荒着吧,就用来种菜。种的最多的是黄瓜和扁豆,架条就地取材,是修剪来的杨树枝。厨房北面,种了两墩丝瓜,它们沿一根细细的铁丝,攀援,到了屋顶肆意伸展,仿佛一溪绿色,流成无边的田野。在厨房里炒菜做饭,绿意是袅袅蒸腾的香气,或者,香气是天上降临的绿意。吃不完的丝瓜,任由它们在阳光下由绿转黄,直至呈现质朴沉定的灰黑,取下来,听得见种子轻敲瓜皮的脆响。些许种子留给来年春天;丝状的瓜瓤柔韧,细腻,丝丝相连,些微粗糙的手感,天作的一套清洗餐具的用品。在厨房和东院墙之间,搭了一个瓜棚,爬丝瓜、冬瓜、葫芦、吊瓠子,也爬扁豆和青虫。进了门口,破旧的小院流红涌翠,镶金嵌玉,自有一种阔大温润的气场。有一年秋天,叶子枯萎,衬托着一个硕大滚圆的冬瓜,活像老家的石碾,在厨房上碾春为秋,却不发出一丝声息。那景象留在心里,让人始终持有对自然和细节的敏感度,以及蓬蓬勃勃的兴趣。
小院里的菜蔬,确证着自我的感知。通过一朵扁豆花洁白的呼吸,内心收获微小的幸福。黄瓜顶着娇弱的花,花的黄,宝石一样熠熠闪光。花谢,瓜熟,自然的秩序这样明朗,这样一目了然,让人明确时间的期限所在,心里不自觉地安放了一个郑重。
城区的田园生活,承接着过去的岁月,像一个人的清谈,说着说着,转换了地点。这种闲散、缓慢的生活,反而催生了我的劳动激情。“那些日子里,闲散是最迷人的产业,产量也最多”(梭罗《瓦尔登湖》),所谓的城市节奏没有俘获我的内心,内收,自控,我如同一只静水里的蚌,内里洁净温润,却不自闭,一翕一张,吞吐扩张着周遭的水域。菜蔬种得用心繁盛。我和从老家带来的种子,很默契地达成从根系走到果实的路程。
是一个寻常早晨。听着小雨在小院里“沙沙”地走着,心里觉得异样的安静。很文学地说,点点滴滴的小雨,直落在我的心里。我竖起耳朵,像一棵菜蔬张开所有的叶子,迎接这来自天上的滋润。隔着玻璃窗,我能看见那种天与地的接纳和孕育。洁净的小雨,安静的菜蔬,它们之间的路径是遥远而又迅捷的。小雨有着植物的属性,它不是高谈阔论,不由分说,亟不可待。沉着镇静,内心温润,小雨是植物的,从容,笃定,在植物的叶脉里走动,悄然无声。叶子青翠。空气清新。我的心就像土地,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刻,一点一点地变软的,身体里的水分让一个人干净,通透,如同静默的植物,有着寻常的绿色,宽厚的接纳。
麦收记忆
赵建红
现在的人每天都坐在空调屋里,面对四季的变化都不敏感了。前几天回老家,看到路边全是晒麦的,才知道又是一年麦收时。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早年一些有关麦收的记忆便被麦秸的清香味牵了出来。那时候我们家人口多,土地也多,一人一亩多地就有十几亩地,算得上是村里土地最多的人家。那个年代,所有的麦地几乎都是靠人工用镰刀收割的。父亲在所谓的国营企业上班,麦收的时候很难请假,姑姑和表弟的地分到我们家,但是人在外地,麦收的时候人是回不来的,奶奶年龄大了农活也是干不了,只能在家里做点吃的,还会给我们准备好多多的凉开水,我只有十几岁,弟弟就更小了,能参加麦收的劳动力就只剩下母亲和三个姐姐了,所以每年快要到麦收的时节是母亲最紧张忙累的日子,所有的准备工作早早就要提前做好了,镰刀早就让父亲磨得闪着锋利的寒光,杈把啦,扫帚啦,各种大大小小的麻袋包整齐摞好,还有扎麻袋包口的绳子都要准备好,放在一个地方,就等着小麦成熟的那天。
等待小麦成熟的那几天,母亲每天都要早早的出去,看看小麦成熟的情况,再回家计算着哪天开始收割。看到人家开始收割了,母亲便一会出去,一会进屋,坐立不安,第二天就把我们从睡梦中喊醒,带上早就准备好的干粮咸菜和水,慌慌地赶到地里,明明麦子还有些青涩,母亲还是看了又看,不知道是马上就下镰好呢,还是再等一天等麦子再熟一些的收割好,一路上迷迷糊糊的我这时候也清醒了,往往会撅着个嘴,对母亲耽误我睡懒觉心里老大不满意。那时候太小,哪里能体会母亲的心情,母亲是要强的人,家里土地那么多,劳力那么少,每次当一整块地里只剩下我们的麦子还站在地里的时候,母亲就急得觉也不能睡了,既不想落后于别人家,又担心万一有个下雨天什么的,几十年前的天气可不像现在这样的干旱,雨可是说下就下的。姐姐们常在母亲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收割的时候劝说母亲再等一天也不急,反正大部分的人家还是没有收割的,于是母亲就会带着我们再回家去,再把所有麦收需要的东西归拢一遍,整齐地放在一起。
还记得我们村有一块地名字叫长千,一个麦畦长度五百米,每次割麦的时候我们总是先收割这块叫长千地里的麦子,母亲割麦的时候像一个冲刺的战士,利索的分工,握镰,弯腰,月牙似得镰刀闪着银光在母亲的手里飞舞。收割的麦地块又干净又整齐,大姐一直是母亲的好帮手,仅仅稍次于母亲。幸亏那时候已经有了大姐夫,每次总是来我家帮忙麦收。大姐夫是个退伍军人,身强力壮的,但割麦的速度与质量都比不上年近五十的母亲,就连大姐也是比不上的,每次当大姐夫那挂满汗水的脸望向玲珑俊俏的大姐的时候,眼里都是满满的疼惜与爱怜,他卖力的弯下腰,想更多更快的收割一些,这样可以减轻大姐的劳累。
母亲每年麦收前都会买上三两个苇笠给我们戴,好像我们戴着新买的苇笠心里会开心一些,干起活来会轻松一些一样。母亲总是戴着最旧的一个,然后是大姐,我戴着的自然总会是一个新买的苇笠,脖子上围一块毛巾,身上长衣长裤,小脸皱结着,和三姐跟在他们母亲他们后面捆麦子。我不知道母亲和姐姐们她们一直弯腰收割是一种怎样难忍的痛疼和疲惫,我只是常常望着远处那长长的麦地,仿佛变得那么的遥远,那大片大片成熟的麦田,翻滚着金色的波浪,在太阳的灼烤下,冒着腾腾的热气,只觉得自己要被这热气蒸发掉了,喝多少水,嘴里都发干,露在外面的手腕和手都被麦芒扎得通红,一个一个的小红疙瘩连成了一大片,又刺又痒又疼,即使是戴着新新的苇笠,也把本来就黑的小脸蛋晒得更加油黑光亮。
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土地,现在麦收的人们再也不用弯腰抢收。联合收割机一夜的轰鸣,就把一大片成熟的麦田脱粒装袋了,那首“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的景象已经远远离我们而去,少了紧张与疲惫,也少了一些热闹和体味。
我生命中的河流
姜佃友
自城顶山山北多个山沟里汇聚而成的这条河,在时光的锣鼓声中,一路冲开泥土碎石,欢快地蜿蜒前行,经过张家溜、胡家旺、青山官庄,在霜山的后山脚下拐了一个大弯,掉头向北,继而转向东南。在西北崖村西南处分为两道,一道自西北崖村前流过,贴着老峒峪村的西侧向南;一道直接奔向老峒峪的村南,两道水流又在村前拉起手,继而向东侧的岳家庄跑去,在岳家庄村前形成一个碧波荡漾的水湾。流水们在这里稍作休息,然后越过堤坝,继续往东而去,经韩家庙子、王坟、管公,到达官庄镇。在官庄分为两道,一道向南成为渠河,进入诸城境内;一道经临浯(在临浯境内叫浯河)流向景芝(获得山东省省长奖的“景阳春酒”就是用浯河水酿造的),最后注入号称山东最大的峡山水库。小时候,我们不知天高地厚,不止一次溯流而上,寻找龙峪河的源头。也曾顺流而下,寻找龙峪河的终点,源头当时就找到了,最终的去向却是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向当地文友电话询问,最后驱车证实的。
如此念念不忘而且费尽心思,可见龙峪河在我心中的地位。它就像我体内最最重要的那条动脉,没有它就没有我的生命(确切的说,没有这条河,河沿岸的百姓都无法生存);没有它,我童年的记忆将是干涩的,没有任何生机和乐趣可言。从这个角度讲,它就是我的母亲,我生命的赐予者和维护者。龙峪河是老峒峪这棵长了千年的大树的根,没有龙峪河的存在,村庄早就干枯而死,成为另一个罗布泊;村庄是龙峪河这根藤蔓上结出的果,因了龙峪河源源不断的滋养,村庄才越长越健壮,越长越饱满。
我迷恋龙峪河的气味,清凉,湿润,带着一丝淡淡的腥气,还有一丝淡淡的香气,就像是青梢瓜清爽的味道,西瓜甜丝丝的味道,鱼汤又腥又鲜的味道。早晨,太阳尚未升起,河面上氤氲着一层薄如蝉翼的雾气,白皙,轻柔,透明,宛若姑娘们脖子上围着的纱巾。这时的村庄就是一个隔着蚊帐尚在沉睡的女子,慵懒,娴静,神秘。公鸡们总是第一个醒来,伸长蜷曲了一夜的长脖子,嘹亮地喊了一嗓子。太阳被惊醒,阳光爬上东山的山顶,扯去了那层朦胧神秘的面纱,村庄睁开惺忪的眼皮,还原本来的面貌。父亲起身,我看见他胳膊上涨鼓鼓的肌肉在晨曦的微光中,有一种让人迷恋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傍晚,当暮霭迈着轻柔的步伐在河面上逡巡,村庄慢慢合上劳累了一天的眼皮。父亲和牲畜们一道踏上了归家的路。父亲身上的肌肉松弛下来,呈现一种疲惫、放松和满足的状态。天幕合拢,星星点灯,月亮仁慈的目光笼罩着这个山洼中的村庄,屋舍,山峦,树木,庄稼,家禽,牲口,还有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死亡的蚂蚁、蜜蜂、牲畜、蚯蚓和号称万物之灵的人——上帝包容一切并宽恕一切已发生的罪过。在这片生长希望也诞生罪恶,繁衍纯朴也滋生龌龊的土地上,上帝超度一切魂灵获得新生。上帝的仁慈心怀在这条河的身上彰显无遗。
河水源源不断地流淌,日子一天天周而复始。流水的脚步暗含了时光的更替,生命的轮回。白发覆盖了父母那辈人的头顶,白发爬上了我们这辈人的鬓角,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衰老中,一个又一个的新生命诞生了。虽然这些年龙峪河的水流越来越小,越来越脏,像是一条被遗弃的腰带,但它依然存在着,流淌着
在这些文字将要结束的时候,我发觉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世上没有名字的东西多了去了,难道我们非要费尽心思给它一一取个名字?有那个必要吗?名字只是一个符号,用以区分或者便于记忆的记号,和它本身的价值,能否打动人的内心没有必然的联系。对那些没有名字的物件来说,存在着,活过了,已足矣。
长的,短的,宽的,窄的,清澈的,浑浊的,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河流,远没有家乡的这条小河记忆深刻。当我踟蹰在过去的时光隧道里,当我跋涉在文字的荆棘密林中,我心里一直流淌着的,就是这条没有名字的河流。我知道,这条没有名字的河流,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