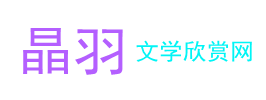鲁迅的样子读后感(祝福鲁迅读后感)
大约记得中学阶段陆续学过几篇鲁迅的小说,《孔乙己》《阿Q正传》《祝福》。当然,我甚至多年来一直以为《祝福》的名字其实应该叫《祥林嫂》。之所以鲁迅会给这篇小说起名字叫《祝福》,就注定是当初我作为一个只把注意力锁定在阅读理解标准答案,进而取得语文考试高分后,以求获得各方夸奖的中学生所体会不到的。
鲁迅向来对自己“文豪”的称号不以为然,在多次演讲中,都表示他其实对文学理论的不通,对于一个学矿出身,后东渡日本学医的“有志青年”,当然不会花太多时间去研究什么写作技巧,以至于以我一个现代人看来,他语言虽辛辣,但可读性一般。不过当然,他的几篇小说写的真是精彩,拳拳到肉,刀刀见血,把人性,或许更多的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中国人的人性,三言两语刻画的入木三分。
小说的开头,旧历年就要来了,这是每个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各家各户按照传统,有条不紊的安排着“祝福”的仪式,期盼着来年的风调雨顺,吉祥安康。这满满的仪式感像极了现在的婚礼。彩礼的厚度,门口井盖上红纸裁成的形状,进门跨火盆先迈哪只脚,说“我愿意”的时候声调高低都要量化。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本地的、外地的,各种仪式杂糅在一起,好不热闹。一定要按“规矩”来,不然因为贯彻不到位走了霉运,可别怪司仪没提醒到位。当然小说中的“祝福”也只是依照旧社会的老制,还不至于让耶稣基督进来插一杠子,不然可真是数典忘祖的大不敬了。
祥林嫂的出场属于小说中标准的倒叙,“她分明已经纯乎一个乞丐了”。乞丐就乞丐吧,鲁迅用了一大串的副词去修饰,可能是想说,祥林嫂起初并不是一个乞丐,而且在变成乞丐过程中经历了“不可说”又“不得不说”的曲折。而祥林嫂接下来的一句话,不禁让我头皮发麻,激起了我继续读下去的欲望,不然任哪个读者都不会对一个旧社会的女性乞丐产生一探究竟的兴趣。那就是祥林嫂拉住文中的“我”问了一句“一个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如果是我在现场,这种灵魂拷问,出现做一个“分明纯乎”的一个女性乞丐嘴里,会让我误认为来者是“地狱”派来的使者,向我索取点什么的。我相信,当时文中的“我”也是一样的反应。于是“我”含含糊糊的回答一句“也许有罢”。紧接着祥林嫂又来一句“那么,也就有地狱了?”直接把“我”问蒙了,好么,果然是和“地狱”有点瓜葛的人。换成是我,已经逃跑了,可是“我”毕竟是认识祥林嫂的,还不至于直接被吓跑。“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祥林嫂问出这句话,连“我”也忍不住,含糊几句就逃跑了。这可不是祥林嫂口中“识字的出门人”能解释的了的了。
跑是跑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已经给心里种下了一颗好奇的种子,可仅仅是种子,没有助缘也是不可能萌发的。“我”果然很快就忘了刚才的“灵魂拷问”,无聊的情绪已经让思绪飞到了城里的福星楼,计划第二天去吃一大盘“价廉物美”的鱼翅了(祥林嫂做女工,一年收入买不了一盘)。可是到了第二天,助缘来了,祥林嫂死了。
在这个年关将至,家家户户都忙着“祝福”的节骨眼,祥林嫂死的是那么的不合时宜。“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这是祥林嫂的老东家对她最后的评价。至此,“我”对祥林嫂的好奇心被填满,对于虽然回到家乡,但是“客居”的身份来说,在这个特殊时间点询问太多“谬种”的问题,终归也是不合时宜的。读者却已经按捺不住想知道“谬种”祥林嫂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这就是鲁迅的高明之处,虽然号称没学过文学理论,但是这种写法正暗合了小说描写的三幕结构。简单说也就是故事背景-冲突事件-冲突解决,然而衔接第一幕和第二幕的就叫做“扰乱事件”,如果小说没有冲突,就不能称之为小说,而只能称之为日志。必须有一个事情打乱安稳的现状,在《祝福》中,祥林嫂的“灵魂拷问”是一个标准的“扰乱事件”,而光扰乱还不行,还必需要把主角一脚揣进一扇门里,让他不能再回到安稳的现状中,那么,祥林嫂的死,无疑就是这一脚,而她再也不可能回来了,进而带出了祥林嫂从初来鲁镇开始的一系列经历。从这开始,情节交还给了主角。
祥林嫂的鲁镇初生活是充满阳光与希望的。她模样周正,手脚勤快,二十六七岁的年纪,一个女人顶的上一个男人的工作量,女主人非常满意,弥补了她自称“寡妇”给男主人带来的不满。然而,她不爱说话的表现,闪烁其词的表达,就表明这个女人积极勤快的背后是有秘密的。果不其然,她是“逃出来的”,被夫家几个人抓了回去。这个“逃”字用的妙。至此,祥林嫂故事线第一幕结束。因为祥林嫂的忽然被带走(淘米的笸箩还在溪边,没来得及收),让东家上上下下乱了手脚,连饭都得女东家和少爷配合才能做出来。而新雇来的女工,大抵非懒即馋,像祥林嫂这么敬业又不图回报的女工不好找了,这就是她在鲁镇做女工的最高价值。
被抓回去后,夫家为了她小叔子结婚的彩礼,反手把祥林嫂“转嫁”给了别人。说“转嫁”有点客气,其实就是给卖了。卖了多少呢?八十千,相当于“物美价廉”的鱼翅几十盘。这里鲁迅讽刺起来连自己都没放过。祥林嫂当然不依,异乎寻常的哭、闹、不拜堂,一头撞在香案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我在想,如果我不愿意干一件事,会不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答案是够呛。然而,即使这样的激烈,换来的也只是女主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这有什么依不依,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
这让我想到了农村杀猪,就是猪跳墙跑了,也会被全村人再抓回来,挨上那致命的一刀,猪有的选吗?我不知道祥林嫂会不会看到杀猪的时候想到自己。又或许,我们自己看杀猪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自己?可是现在都是机械化杀猪,赶进去的是猪,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包装好的香肠了。杀猪都杀的这么文明,这么高科技,没有红色的血,可能多数人还会觉得欣慰。
没想到祥林嫂又回鲁镇了。第二任丈夫也死了,死了一个,又死一个。她的儿子,唯一一个可以让她翻身的筹码,也被狼叼走了。她瞬间变成了既克夫又克子“不祥之物”,夫家人当然可以以此为理由赶他走。当初寻死觅活不想嫁过去,这一回不想走更不可能了。重回鲁镇,她最初还是有剩余价值的,女主人对她的好感还在,然而祥林嫂自己的核心价值已经不在了,眼睛没有了神采,手脚也不再灵活,关键的关键,因为她的不祥,男主人已经不让她参与家庭最重要的祭祀仪式了。
人除了活着,在价值体现上最重要的两点就是“被认可和被需要”,她为什么不厌其烦的和周围人叙述儿子被狼叼走的详细经过,就是她要在“被需要”这个价值已经所剩无几的情况下,通过出卖悲惨经历,获得更多的认可。然而,她不明白的是,情绪价值是易耗品,如果没有持续的输入,总有一天也是要被消耗殆尽的。所以,在她无数次的透支她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的故事后,换来的是嘲讽、奚落、侮辱、践踏。
她以为去土地庙捐门槛就能消掉她一身的“原罪”。可当她花完一生积蓄捐了门槛,兴冲冲想去参与东家的祭祀活动,“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被女主人一声大喝“你放着吧,祥林嫂!”之后,她最后一点“被需要”的价值感也崩塌了,至此,她最后的一点抗争的勇气也没了,沦为了一具“行尸走肉”。而在最后一点价值被榨干后,被东家“打发走”,沦为 “她分明已经纯乎一个乞丐了”。而她见到“我”之后的最后一问,以及“我”含糊的回答,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油尽灯枯,祥林嫂死了,可最终连死都被人嫌弃。
学界评价鲁迅对中国基层民众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完全同意。这八个字透出来的情绪是无奈和绝望。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就是要启发民智,白话文运动也好,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也好,在文艺方面的矫枉过正也好,都是想引导民众通过“有文化”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虽然当时中国受教育程度大大增强了,但是民智又真的开了多少呢?同样的套路,披上一层华丽的外衣,不就又可以堂而皇之的吃人了么,只不过吃相越来越好看了。而被吃的人,却还在努力的为争取一个前排更容易被吃的席位“内卷”着。
鲁镇的“祝福”还在进行着,“祥林嫂”的尸体没有地方扔,只能暂时以天为帐,以地为床,倒是符合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但是虽然境界这么高,这“祝福”于“她”,或者“她们”又有多大的关系呢?
所谓众生平等,每个人都值得活着,有句话说得好,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但又并不是每个人都活得值得。就像是祥林嫂,如果没有死,那活着可真的就是对她的诅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