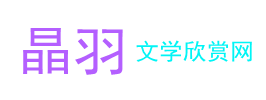北朝别开生面的散文著作
曾在洛阳住过的诗人,几乎构成了整个唐代文学史,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京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北朝别开生面的散文著作1
唐诗永远说不尽。这是我们时常听到的感慨,也是真实的私人阅读感受。唐诗之所以述说不尽,并非仅仅因为唐诗浩瀚无垠,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对它有无尽的需求和想望。当下社会无论多么“现代”,唐诗所承载的深挚情感、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总能在我们心中引发回响。
当踌躇满志时,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所描画的形象和心理正是我们想象中的自我形象;当遭遇人生困顿时我们发现,杜甫“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中所积聚的沉郁之情时隔千年依然动人,依然有效。甚至有些诗句我们难解其义,只读文字本身,心灵就近乎本能地起了响应,比如李商隐的那些诗句,哪怕你已无法记起,也很难忘记那些诗句留下的迷离柔软的伤感。
如何走进唐诗,每个人有不同的路径。作家马鸣谦的《唐诗洛阳记》从千年古都洛阳这一视点看向唐诗,追索洛阳在唐诗发达繁盛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梳理与洛阳有关的诗人们的行迹,探究唐诗的演变与书写和洛阳这一地理空间之间的必然性关联,让我们获得了阅读唐诗的新视角。
在此次采访中,关于洛阳为什么对唐诗和唐代诗人们如此重要,马鸣谦说:“正式将文学纳入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是从武则天和唐高宗时代开始的,而且就在洛阳。这使洛阳成为一个文化的培养皿,对天下读书人形成了吸聚效应。就像现在的北京和上海有很多北漂或沪漂一样,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洛阳和长安这两个都市圈或周边定居落户、繁衍生息,他们的子孙后代又在那里成长,文化教养的基础就这样打下了。”
马鸣谦,生于苏州,祖籍浙江绍兴,作家、诗人、译者。著有长篇历史小说《隐僧》《无门诀》《降魔变》等。小说创作外,也从事文学译介,已出版奥登文集译作三种,分别是《战地行纪》 《奥登诗选:1927—1947》和《奥登诗选:1948—1973》,此外还译出了狄更斯小说《双城记》和《松尾芭蕉俳句全集》。近10年来潜心钻研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计划陆续写成以唐代诗人杜甫、李商隐、白居易为主题的“诗人传三部曲”。《唐诗洛阳记》2本正是小说三部曲的真实背景与历史舞台。
从地理空间来观察唐诗
新京报:本书的写作缘起,是你和几位友人聊天时“认领”的选题(洛阳之外,还有长安、成都和扬州)。除了这一原因,选择从洛阳的视点探究唐诗的原因还有哪些?
马鸣谦:这本书的缘起确实有些偶然,但回顾起来也不是意外。当2019年我和柳向阳、茱萸两位诗人聊到这个话题时,我刚把《降魔变》写完并出版。在准备写《降魔变》之前,我也一直在做“诗人三部曲”(以杜甫、李商隐、白居易为题材的小说)的准备工作,差不多是在2016年前后,我把陈贻焮先生的三卷本《杜甫评传》细读了两遍,起心动念准备“诗人三部曲”的首部。那段时间我对很多唐代诗人的行迹,主要是对杜甫的行迹非常感兴趣。你在网上也能看到杜甫的行迹图,从他出生到壮游江南,包括后来游齐鲁、游梁宋,一直到入蜀和出峡,他一直在地理空间的迁移中完成诗的书写。在这个准备过程中,我对地理空间变得非常敏感,而且越来越发现,诗人生活或旅行的地理空间与创作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
如果我们从地理空间来观察一个时代的文学,比如唐诗,我们会发现,跟乡村比起来,它大部分还是在城市里完成的,或者就是在从一座城市到另外一座城市的过程中完成的。张定浩兄提名《唐诗洛阳记》入选“行读图书奖”六月榜单时所写的一则评语把这一点揭示得比较明白,他说:“当代流行为城市作传,这本书也可称为一本别开生面的洛阳传,它提醒我们注意,中国的古典诗歌和大城市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厚。”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触到了我写出这本书的部分用意。
《唐诗洛阳记:千年古都的文学史话》,马鸣谦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
我本身的写作和翻译是比较跨界的,古今中西都有涉及。我曾读到翻译引进的《伦敦文学地图》《巴黎文学地图》以及《伦敦传》这样的书。另外一个外部刺激来自日本,日本有非常多汉学家和作家会写到中国历史题材,我一直在观察他们在这方面的优点。日本同题材的写作都要比我们早,研文出版就出过植木久行写的《唐诗的风土》,这本书就跟文学地理有关,植木久行在讲谈社学术文库还出过一本《唐诗岁时记》。相比而言,我国作者在这方面的写作意识是比较落后的,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外部刺激。要知道,“风土”和“岁时”这两个文化观念本就来自中国本土,只是我们忘失已久。我以前曾讲过,自己的很多写作是以耻感为出发点的,本国古典文学里那么好的写作资材我们没有去用,太不可思议了。无论从私心还是公心来讲,我都觉得有必要填补这一空白。
另一方面,回顾我们的古典文学,古代文学史都是跨朝代、大时段的,单独的唐诗文学史好像不多,只有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相当于做了一个开创性工作,非常难得。有关唐代的城市文学史好像也没有,有关长安和洛阳在唐代文学史中的影响和地位,有零散的单篇论文,但从整体来看似乎也存在着一个空白。为了解这两座唐代都市的空间,我细读了清代学者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徐松的这本书是开山之作,他发心写这本书的目的在《自序》中就已挑明,是为了“吟咏唐贤篇什之助”,他把它理解为工具书,他有明确的写作对象,即唐诗的读者们:你们不是喜欢唐诗吗?你们可能对诗里写到的空间都不了解,那我来帮你们调查清楚。要写成这样一本书,当然需要比较综合性的文化学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真的有必要打通各个彼此相隔的领域,我自己就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城市地理的内容与唐诗文学贯通起来。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载《隋唐洛阳城图》。
有关写作用意,我还想强调一点,这套书分上下两卷,文字量很大,之所以会如此铺展开来其实也带有我的另一个写作意图。这里分享两个词,一个是scenario,有“情节”“场景”“前景”的意思,也就是视觉性的方面,我要写的东西我自己必须要看到(写小说时也是如此)。还有一个是panorama,是“全景图”的意思。确定好写作题目后,我花了大量时间来搭设这本书的scenario和panorama,我要想象并看到它的全景。我觉得自己找对了目标:相比长安,洛阳真的是唐诗发达繁盛的一个培养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动力来源。
八月初,荣新江教授来苏州找我聊天,他拿到《唐诗洛阳记》时也很喜悦,因为这本书某种程度上也响应了他的研究方向。荣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采用读书班的方式,将长安的每个里坊都像徐松写《城坊考》一样做深度的资料研读,我这本书跟荣教授的都市史研究方向是一致的,因为他们摄取材料的方向除了官修史书、地志、方志以外,文学方面的材料也有调用。而《唐诗洛阳记》的重心是文学材料为主,再辅以其他的史料和地志资料。
新京报:洛阳的哪些元素刺激了李白、杜甫、韩愈等如此多的大诗人们的写作?
马鸣谦:就像现在的北京、上海,吸收接纳了很多大学院校、学术研究机关、出版社、刊物等文化机构。与此类同,我们转移到唐代会发现,洛阳和长安具有同样的功能,具有相当强大的吸引力,对于要从科举求得上行通道的士子来说,它就是天下的中心,对商人来说也是如此。
我在书中特别单列了唐诗发达的三个要素,其中就有提到科举的完备(其他两个要素分别是氏族的调整和类书的发达)。回顾整个唐代史我们会发现,洛阳恰恰是科举制度趋于完备的地方,当然,长安也一直参与其中。我们要知道,正式将文学纳入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是从武则天和唐高宗时代开始的,而且就是在洛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使洛阳成为一个文化的培养皿,对天下读书人形成了吸聚效应。就像现在的北京和上海有很多北漂或沪漂一样,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洛阳和长安这两个都市圈或周边定居落户、繁衍生息,他们的子孙后代又在那里成长,文化教养的基础就这样打下了。
你提到了杜甫,他就是个标准的“洛阳仔”。我在《怀洛之思》一章列了一张清单,发现住在洛阳或者住在洛阳附近,或者曾经在洛阳住过的诗人,几乎构成了整个唐代文学史。这是我之前没有料到的,也印证了我的直觉:洛阳真的在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大诗人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唐诗繁荣的原因
新京报:这本书主要写唐诗,但由隋朝写起,其中写到一位重要人物隋炀帝杨广,有人评论说,读这本书不料被隋炀帝圈粉了。隋炀帝在东京洛阳的建成以及相关文化建设方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马鸣谦:唐和隋经常可以联系在一起考虑,因为两朝统治者的血缘关系非常近。关陇军事贵族取得天下、建立隋朝以后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整合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南方文化即以六朝文化为核心),融汇成一种新文化。杨坚在杨广很小的时候就把他派到南方担任高职,驻扎在江南,给他配的妻子是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所以杨广的婚姻就是一个北朝和南朝的结合。这是一场政治婚姻,也是一次文化婚姻。借用段义孚先生的“恋地情结”,我也写到杨广的恋地情结:江南虽然不是他的出生地,但他非常喜爱、眷恋江南,所以他才会在父亲杨坚去世后力主从长安移都洛阳,因为洛阳离江南更近。包括开凿大运河,都是为了接通他在少年时代生活了很长时间的江南。虽然对杨广历来有很多负面评价,但客观来讲,这些举措在推动中国文化的南北合流、获得文明的持续上升方面,其实是起了非常大、也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杨广在文化建设上的建树也很多,包括编类书、城市建设。我们经常讲,历史是由民众推动的,可是,仔细观察又会发现,其实很多时段乃是由那些富有直觉本能的所谓关键人物来推动完成的,杨广就凭着他的直觉判断有力推动了南北融通的隋唐文化格局的形成,也间接引燃了唐诗创作的“文学爆炸”。
《唐诗洛阳记:千年古都的风物之美》,马鸣谦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
新京报:前面讲到唐诗繁荣的几个原因,包括氏族的调整、科举的完备、类书的发达。还有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马鸣谦:就像我刚说的,关键人物、大人物创造历史。《唐诗洛阳记》里给了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单独的篇章,这些篇章列出来是有提示意义的。对于一个朝代或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这个时代的某些决定性人物是可以施加很大影响的。隋唐的帝王强调文化教养,这不只是施之于民众,要普及教化,他们首先要求自己和皇室成员这样做。比如战乱一结束唐太宗就拼命补课,他年轻时四方征战,没空读书,后来就开始恶补,而且非常用功。执政者在文化教养上的自觉的学习心态,以及他们对文学创作的倾心投入,所起到的示范作用是无可抵挡的,特别是在古代传统社会里。他们知道治国需要用才,而用才就需要选拔,他们接受了比较健全的文化观念的熏陶,在文学上又有自己的看法和理想,于是把文学纳入科举科目才会变成顺理成章之事。这种对文化和文学的重视是一种价值观的建构,会慢慢向其他阶层渗透,甚至直达最基础的乡村。
新京报:在唐诗发达的几个要素中提到类书的发达,是个比较有趣的现象。类书类似随身卷子,诗人们写诗时有时会翻一翻,激发灵感。你怎么看这种创作方法?
马鸣谦:类书我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的,有的很大众化,为了普及基本知识和教养,这样的类书提供了唐代人的整个知识图景和视野;另一类是单纯的文学类书,其中比较重要的文学类书就是对杜甫影响特别大的《文选》。各种各样的文学类书其实是文学入门的重要桥梁(就像现在我们读文学史或作品选本一样)。除了官方的大部头类书外,民间还有很多小型类书或者自编类书,比如如果家族里读书的孩子比较多,他们自己会编制类书。这种风气是文化教养开始生根发芽的信号,也熏陶了很多诗人的写作。
很多唐代诗人除了早年读文学类书比较多,到后面写作诗文的时候也会用到,比如李商隐,就会调用对他写四六骈文比较有用的类书(他在骈文方面的老师令狐楚就有自编的《表奏集》)。在这个层面来讲,也可以把类书理解成参考书。另外,所谓“随身卷子”也是个人使用的小类书的一种,那多半是为了摘抄前代诗人或作家的好文句,以便日常的琢磨和研习。
杜甫:
有感情、有热爱、有好奇心的人
新京报:在对唐诗,尤其是与洛阳有关的唐诗之发展做了综合论述之后,本书就进入了具体的诗人领域。第一个是陈子昂,追慕汉魏风骨,提出复古观念,成为“初唐文学自觉的先声”,对后世影响深远,获得一波又一波的回响。陈子昂提出复古主张的背景是怎样的?为什么是陈子昂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逆行者”?
马鸣谦:我想提醒读者留意陈子昂之前的两个章节,因为我特意写到了宫廷诗的重兴,这个篇幅的容量或许可以回答你的问题。隋唐时,杨广也好,李世民也好,承续的还是六朝贵族文学的余波,而这余波在初唐却是文坛的主流。皇帝这样写,他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就这样写,他们都在讨皇帝的喜欢。这种风气从唐太宗到高宗,到武则天接掌权柄后也是一样。
所谓贵族文学就是六朝的文学(也可简称为“齐梁文学”),追求唯美,讲究辞藻,写得比较空洞,题材也较偏狭,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狭窄,一年固定的就那么几个节日、那么几个场景,写这样题目的诗是比较模式化的,文学因此丧失了内在活力。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宫廷诗,没有唐前期宫廷诗的重兴,就没有后面盛唐、中唐和晚唐诗的繁盛。陈子昂提出复古观念,背景就是宫廷诗的重兴和壮大,以及整个社会主流对文学的重视和认同。物极必反,宫廷文学达到极盛,肯定会有人要往另外的方向走。
另外,陈子昂的这一选择也和他仕途遇挫有关系。如果武则天或者后来的皇帝给他较高阶的官职,情况也许就不一样了。陈子昂以及杨炯、骆宾王等人,他们都是被抛离都市圈的文学侍从之臣。因此陈子昂的“逆行”,既是文学观念的自觉,也是由个人生涯的沉浮所决定的。如果长久留在宫廷,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要在文学上发言的欲望了。恰恰因为被抛离了中心,张力就产生了。
新京报:写洛阳诗人,杜甫不可或缺,他的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有“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样的名句,极为生动地写出诗人归洛的急切又兴奋的心情。关于伟大的杜甫,有关洛阳之外,还想拓宽一点视野。你也正在写一部关于杜甫的小说,能不能谈一谈这部作品的起因、规划等?你如何看待杜甫的人生和诗歌写作?
马鸣谦:关于杜甫题材长篇小说《征旅》的缘起,前面已提到我研读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的情形了。这次细读非常重要,让我第一次跳出了以前读唐诗时单篇赏析的那种局促狭隘的视野,完整看到了杜甫作为诗人的整个人生,反过来,也让我探入了杜诗的内面内层。这种感受比之前任何一次阅读都要来得明确和强烈。这深深触动了我。
在去年年底写成的这部小说中,我选了杜甫后期停留在云安和夔州的时段,再以此为主轴,折射了他的一生。他在洛阳的早年生活也写到了,包括你提到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以洛阳作为想要回归的故乡的明确方向。
为什么选择杜甫的夔州生涯来作表现?如果对他一生的创作有所了解,我们会发现,要找一个写诗最密集的时间段,那就是在夔州。三年不到的时间里,杜甫写了四百多首诗,差不多两天一首。在世界文学史上,我们找不出第二个人,也找不出第二个时段,像杜甫的夔州时期这样写诗,这简直是文学上的奇迹。最关键的是,杜甫在夔州迎来了他最重要的上升,他的三分之一,甚至将近一半的杰作都是在夔州写出的。像我们耳熟能详的《登高》,我每次诵读时都能感受到他强烈的感情。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用苏州话吟诵,用普通话吟诵,代入感特别强,恍若某种精神上的附灵。
除了创作密集,我想强调的另外一点是,杜甫在诗中写了他大量的真实生活,这是之前的诗人没有做过的,后面的诗人几乎也没有达到。后来南宋陆游有追摹效仿,诗作数量比杜甫的存诗翻了有两三倍,可是,从原创性和饱满性来讲,还是老杜更厉害啊!日本的夏目漱石等现代作家从传统文学过渡到现代文学时,曾有提倡“私小说”的观念,按照我的个人理解,近一千五百首杜诗里面就很有类似“私小说”或近代小说的色彩,他的诗有很强的叙事因素。真的非常幸运,杜甫已经为我提供了足够多的写作资材。小说中写到的内容不是我凭空的遐想,而是基于杜甫诗文中的真实生活线索来做的发挥和勾连。我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就是要让杜甫的人生变得更饱满、更充实,让他变成一个活生生的、我们可以理解的“当代人”。
蒋兆和《杜甫像》。
说到如何看待杜甫,我把他理解成一个天生好奇的人,他从来没有丧失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我也希望大家认识到,杜甫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人。很多约定俗成的文学观念或文学解说总是把感情当作很次要的因素,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感情是个很重要的推动因素。包括我能够发心来写《唐诗洛阳记》和杜甫题材长篇,也是如此。倘若人无深情、长情,做事也不能长久吧。
我在小说里写了很多杜甫生活中带有喜剧性的场景,比如他喝醉酒回家,从马上摔了下来,养了好几天伤,很多官员携酒来探望(详见杜甫《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从类似的很多生活细节中,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有感情、有热爱、有好奇心又有趣味的人。这也促使现在的写作者思考,你的感情资源在哪里?你认同的感情资源在哪里?如果你的认同不足够,那么你的写作可能也走不长。现代文学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无情,把人抽象为冷态的固化的观念。如果观念里不带感情,它也是很单薄的。我经常会讲一句话叫“感情与继承”。有感情你才会去继承。我们的文学阅读,一般只会包裹在当代流行的氛围中,被各种各样的“时流”所迷惑,往上回溯到“五四”就已经很好了。这是很不够的,我们的阅读必须跨越全时段的整个汉语文学,我们必须唤醒汉语文学中无数出色的灵魂和他们的作品,这才是完整的文学教养。
李商隐:
最内向化的唐代诗人
新京报:来到中唐,以韩愈为首的“怪奇邦”令人印象深刻。这些人的诗多怪多奇,书中引到的一首韩愈诗,艰涩拗口到让人惊讶。这一小群诗人之所以选择有些偏狭的怪奇之路,原因是什么?这一章节中令人动容的是几人之间的友谊,你怎么看待诗人之间的友谊?
马鸣谦:这和上面讲的陈子昂有类似之处。韩愈他们的出身阶层都不算很高,都不是所谓的“高门子弟”,在中唐的官场和都城生活里没什么地位。韩愈很有趣,他是一个外向型的人,特别能交朋友,他曾在自己的文章里盘点过大概数目,在长安若干年里交了有一千个朋友。他采取的生活策略和写作策略显然都是有意识的。从现实层面讲,他能联络到的朋友越多越好,以此造成声势,产生社会影响,这对他官职的升迁是有利的。在文学上,他也要发出声音,而且文学的声誉对他的仕途也有帮助。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他们去世后,大历年间的那些诗人相对来讲比较平庸,个性色彩不鲜明,出现了保守倾向。而在韩愈那个时代,名声比他更大的是一对驰骋文场的好友元稹和白居易。他们两个已经冒了头,天下皆知他们的文名(白居易的诗就更是流行,连里巷妇孺都能记背),韩愈就想自己该怎么办?恰恰是来到洛阳的这段时间里,他有意识地选择了这种“怪奇”的写作策略。
文学上走这么怪奇的路线也把“复古”往前又推了一步。“以文为诗”写作观念的提出,唤起了一种变革之心。韩愈对四六骈文是很反感的,他和柳宗元一道提倡古文,是对当时主流的官场骈体文的反抗和反拨。他们发现,用散体来写诗也可以写得很好,甚至比原先那些人写得更出色。
我对洛阳“怪奇邦”有一点是很肯定的,他们非常勇敢,在保守的、有着很多范式的诗歌写作上做了大胆的突破。
从诗人之间友谊的角度看,我高度赞许韩愈的品格。他任官后一直在接济周边的朋友,他对待友谊的方式很值得我们关注和看重,也是我们当代的文学空间里应该学习的地方。文学友谊非常重要。但它绝不是酒场饭局上的应酬,文学的友谊是指对彼此作品、思想和价值观的认同,作品价值居首,社会价值其次。这个顺序不能颠倒。
新京报:书中写白居易的章节也许是最有情、有趣的一章,因为写到白居易漫长又感伤的青春自由恋爱史,以及他中晚年的私人生活,还有被索鹤、索马等趣闻。尤其是白居易那段失败的恋爱,你认为对他之后的生活乃至创作观念都有重大影响。
马鸣谦:白居易的诗留下来很多,我细读、梳理过后发现,他和杜甫有类似的一面,他在诗里也记录了很多实实在在的生活细节和感情,特别是感情。在中国文学史上,单独表现一段持续很长时间的恋情的,白居易好像是第一个吧。可作比对的还有李商隐,他有很多诗也都和恋情有关。现代人的意识生成的表征之一,就是感情的自我选择,欧洲浪漫主义早期的文学很多都是写恋爱题材的,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恋爱题材对于白居易和李商隐是指标性的,恋爱对他们写作和人生的塑形作用非常之大。他们在这方面的写作提示了中晚唐时期人文观念、社会观念、婚姻恋爱观念的重要突破。借此管窥,或许可以将其理解成文学近代化的某种征兆。手头正在写李商隐这部小说,篇幅会短一些,名字就叫做《少年李的烦恼》。
李商隐像。
新京报:书中写到李商隐时,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注释中说,李商隐一生写祭文54篇,为唐人之冠。善于写祭文只是因为他辞章华美,还是其中透露出李商隐的某种内在情感特质?读他的一些诗,总感到有死亡的阴影存在其中。
马鸣谦:你的猜测部分是合理的。我会把李商隐定义为唐代诗人中相对闭合的某种类型,而他是其中最内向化、内敛化的一个。写诔奠之辞其实并不是他自己选的。他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跟着恩主令狐楚,用四六骈文写作各种章奏书启,后来也给别人写祭文、碑志,写这些公私文章用的都是流行的骈文,他从小就受了训练。刚才说过,他的诗是相对闭合的、内敛的,而当我们去看李商隐写的祭文,就会发现他在文章里涌流的强烈的感情,特别是为自己亲人所写的祭文,其表现强度要远超过读他的诗(比如那篇《祭小侄女寄寄文》)。他的诗反而像迷一样,不会让过多的个人色彩外溢出来。在这些祭文中,我们最内向的诗人透露了他最真实的感情。他的感情之深之强可与老杜一比,只是他经常会将它们掩盖起来。
李商隐撰并书《王翊元夫妇墓志铭》,宜阳鱼元弼刻字。作于大中三年(849),李商隐时年38岁。王翊元是王茂元之四弟,李商隐妻家的长辈。
《降魔变》,马鸣谦著,大方|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
洛阳:
文学的都城
新京报:《不尽的尾声》一章写道,“在晚唐诗人的书写中,洛阳渐渐脱离实在的情境,笼罩上了一层浓厚的历史记忆的翳影,它们追忆与想望的,是洛阳灿烂辉煌的过去。”这大概也是今人从历史和文化层面想到洛阳时的所感所想,洛阳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你如何看待作为某种象征的洛阳?
马鸣谦:我从直觉出发写作,写下了《唐诗洛阳记》。在此过程中上溯我们的文化根脉源流,试图重新找回这颗“华夏之心”。洛阳是文学的都城,艺术的都城,作为历史文化地标,洛阳的地位无可动摇。另外,我也希望这本书可以让读者在读唐诗时,能有意识地进入一种空间性与历时性的思考。
最后还要提到我的一个发愿。九月我会去洛阳做一场首发活动。我可能会通过某种恰当方式,建议洛阳方面的朋友把诗碑建立起来。我前两年译出了《松尾芭蕉俳句全集》,芭蕉句碑包括其他诗人的句牌,可以说遍布了日本国境。每到一处,作为旅途一景,大家都会读一下刻有诗句的诗碑,这种无形的文化熏陶特别重要,很值得借鉴。文学能不能进入我们实在的城市空间与生活空间?当然可以,这也是《唐诗洛阳记》两册所包含并希望达成的另一层用意。
采写/张进
编辑/走走 青青子
校对/杨许丽
北朝别开生面的散文著作2
《见南山:田园诗史话》
蔡丹君 著
一部田园诗史,就是一部中国士人的精神史
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无不入诗
田园中的一枝一叶,一鸟一虫,
承载了几千年的诗意起兴
焦秉贞 历朝贤后故事图 葛覃亲采
《见南山:田园诗史话·序》
《田园诗史话》是一个有趣味的题目,虽然要贯通诗史,却不是写诗史。
“话”字带了几分聊天的意味,因此在讲史中还要有话题。这对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来说,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专业研究有自己的套路,如果写田园诗史,必定要从先秦到清末,从田园诗发展的外因内因到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搭好架子,全面铺开。结果可能会写成一本厚重的大书,却未必有多少读者能感兴趣。而这本史话限定在十万字,即使仅把历代田园诗全部罗列介绍一遍,篇幅也不够。况且唐代以前,诗歌数量还有限,宋以后的诗集则浩如烟海,要从中将田园诗筛选出来,恐怕旷日持久也难毕其功。
作者颇具慧心,为全书编织的经纬是:以先秦到明清的若干历史阶段为“经”,以“农事”“物候”“躬耕”“归园”“乡居”“造画”“悯农”和“别趣”八个主题为“纬”,这就将田园诗的“史”和相关历史文化的话题都包含进去了,既摆脱了诗史写作的框架,又获得了闲话的自由。
由于全书经纬的方面广,跨度大,作者在讲述与田园诗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时,自然会有不少新的收获。例如,关于先秦的农事诗,研究田园诗的学者一般只视之为源头,极少从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这些诗的内容,作者则认为“田园诗中,有一部中国农业经济史。”她联系先秦文献和出土文物,解释《诗经·大雅》中的“载芟”“良耜”等诗篇中所提到的耒、耜、镈、铚等农具,以及所种植的百谷、蔬菜、水果、乃至所用调味品等等 ,同时将天子籍田、祭神等礼仪与农事联系起来,指出“早期歌谣基本上是围绕田间祭祀展开的”,使读者透过古人艰深的文字看到了具体生动的田间劳作和祭祀的场景。
辋川图
除此以外,她还认为田园诗史又是一部自然物候史,士人的精神史,中国农村社会史。透过这些视角,本书时有大小不等的创获,比如,从“物候”的角度,注意到曹植对田园的关注;从陶渊明的社交圈,看出颜延之与江州文化圈的关系及其对陶渊明作品早期流传的影响,指出与陶渊明交游的“邻曲”不少是基层文化士人。又如,通过追溯东汉以来庄园经济发展的脉络,观察到 “田”与“园”分出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文人与“园”的关系,也可分成躬耕者之“园”和栖居者之“园”两条线索,“园”往往为诗人提供停驻下来思考人生的空间。由此分析了谢灵运和谢朓欣赏田园的不同角度和体悟,甚至还有沈约、范云、何逊、阴铿、徐陵等诗歌中的田园描写,这不仅对于山水田园诗研究的空白是必要的补阙,而且从中发现了田园诗概念的裂变。
由于盛唐以前的田园诗在陶渊明和王、孟手中形成了摆脱尘网、回归自然的基本主旨,以此界定田园诗的论著,最多只将“史”写到韦应物、柳宗元为止。从安史之乱开始多见的“悯农”主题在文学史中向来是被列入新乐府一类反映现实的诗歌中的。从田园诗研究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一种缺陷。
本书将这类诗歌列入田园题材,以杜甫作为开端,认为“在田园诗中,杜甫塑造了多面的自我形象。他时而是忧患乱世民生的虔诚儒者,时而是退居田园的疏放隐士,时而又是寄人篱下、举目无依的漂泊者。杜甫多样身份的切换,造成了他的田园诗中也交织着多样的主题。”不但指出杜甫在唐代田园诗发展中的转关作用,也使中唐大量的悯农诗在杜甫之后进入了田园诗的范畴。
而从这一角度来看新乐府,又可以得到更深切的认识,比如作者指出:“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以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田家之苦越来越受到文人关注,‘悯农’诗大获发展。中唐以后‘新乐府’运动的发生,也和这一时代背景紧密相关。”所以“‘新乐府运动’首先抨击的,就是两税法”。
这就解释了当时为什么出现那么多抨击赋税繁重之弊的诗歌,为什么会如此细致地刻画农村凋敝的现实和农民的困苦。与此同时,本书还将这一时期悯农诗中涉及的灾荒、徭役、减户等内容,与中唐官僚机构臃肿、军费剧增、藩镇割据等严重社会问题所造成的恶果联系起来,从多个角度说明了“传统田园诗中所表现的对田园的倾慕和向往,被中唐诗人尤其是参与到新乐府运动中的诗人完全打破”了。
豳风图
由中唐悯农诗顺流而下,本书还对宋代田园诗如何在悯农的传统上,继续发挥其批评时政的作用,作出了客观的剖析。既承认其体现士人社会良心的一面,也指出其成为新旧两党进行政治斗争工具的一面。
在谈及南宋田园诗的发展时,本书肯定了江湖诗派的推动作用,认为“这些人的诗歌,深受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的影响,对农村的风土人情有非常深刻的表现。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是刘克庄”,同时从封建租佃制取代庄园农奴制的变革,劝农、行春的职官制度以及祠官制度等方面分析了宋代田园诗不同于前代的社会背景。
因此,虽然从中唐到两宋的田园诗,本书仅用一章“悯农”来概述,但仍然清晰地区分了各时段的不同特色。关于明清的田园诗,本书所费笔墨较少,但用“别趣”这一主题概括了“在市民文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大环境下”,田园诗仿古与创变并存的特殊风貌,特别关注士大夫借田园抒发人生别趣的诗歌,还是抓住了发展的大势。
本书在勾勒田园诗发展的轨迹时,较偏重于历史社会背景的阐释,但也很善于通过一些作品的具体解析,说出不同时代田园诗人的主要特点和差异。例如在分析王维《渭川田家》的最后两句“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时,作者指出:“诗人一边说‘羡’此悠然,一方面却逃不开徒有羡慕、不能融入的‘怅然’。心理上的矛盾,正是所拥有的生活与所向往的生活之间的距离。所以,王维是归不去的。唐人对陶渊明式田园情调的体认,是停留在欣赏层面的,不可能做到彻底实现一种生活选择上的替换。
田园的风光,在唐人笔下,只是一种心情,不是一种实在的生活。”这就精辟地点出了陶诗与盛唐田园诗的基本区别。又如举出储光羲的《渔父词》和《吃茗粥作》说明其田园诗的两种风格,认为“储光羲观察田园的视角,比王、孟要更为精细”,“他对田园的观察更为看重实物细节”,“充分表现了田园生活中的人情味,和善与亲切”。在分析杜甫的草堂诗时,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与陶渊明的《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相参看,从“田园诗主题的发展”来认识这首名作,也都体现出作者观察问题善于从人所忽略之处另辟视角的特点。
当然,从陶渊明到王、孟,山水田园诗艺术特色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要在一本小书中时时出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作者的评说处处出于自己的感悟,语言表达也力求活泼生动,所以总会不时有星星点点的火花在字里行间闪亮,令人读来颇有兴味。
清 陈枚 《耕织图》之一
作者在跋文中表示以此书向我致意,实不敢当。拙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草成于三十年前,难免留有诸多遗憾,正希望后来者有更大开拓。丹君在北大攻读硕士和博士多年,我亲眼见证了她在学术上成长的全过程。她敏悟勤奋、思路灵活,读书中常有出人意料的发现。尤其关于北朝乡里社会研究的博士论文,选题角度和发掘深度都超出了一般博士论文的套路,可谓在北朝文学研究中别开生面。这本《田园诗史话》虽是小书,但仍需要阅读大量材料,精心钻研和提炼裁剪,所以学术含量丰富,其中有不少可以继续探索的课题,对专业研究的学者也有启发。
以上只是我在阅读书稿时随手记下的点滴感想,不足以称序,权充导读而已。
北宋马远《芳雨春霁图》
【编辑推荐】
田园牧歌是具有农耕传统的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尤其对于处于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的人们,传统的田园生活更是令人向往。本书梳理田园诗的历史,让读者更加明了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发展脉络,使读者能够更好地欣赏田园诗,理解背后的文化内涵。本书思路巧妙,摆脱了传统的诗歌史写作模式,以深厚的学力和清新的文笔,将田园诗史分为八个阶段,分别总结为一个关键词,颇有洞见性和启发性。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田园诗发展流变的普及性著作,以时代为经,主题为纬,呈现古代田园诗的历史脉络,发掘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与美学意义。
田园诗体现了古老中国的重要精神内核。田园诗史中,有一部中国农业经济史、一部自然物候史,还有一部中国农村社会史,更是一部士人的精神史。
今人可以从中汲取古人热爱自然的心灵力量,既能抚慰匆忙生活中的疲惫之心,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滋养,并弘扬关注民生的人文情怀。
【作者简介】
蔡丹君,1981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方向的研究,出版有《从乡里到都城:历史与空间变迁视野中的十六国北朝文学》《浮世本来多聚散:唐诗中的二十一种孤独》等著作。
【目录】
序(葛晓音)
绪言
第一章 农事
第一节 《七月》
第二节 天子与农人
第三节 南亩百谷南山蕨
第二章 物候
第一节 《月令》与思念
第二节 春木、谷风与黄鸟
第二节 桑间故事及其他
第三章 躬耕
第一节 陇亩之民
第二节 柴桑故人
第三节 复得返自然
第四节 何处望桃源
第五节 望、见南山
第四章 归园
第一节 山水庄园
第二节 朝隐与园憩
第三节 上巳节诗咏
第五章 乡居
第一节 北土园田风俗
第二节 京畿与方外
第三节 寓北者之“小园”
第六章 造画
第一节 盛世优容
第二节 东皋薄暮望
第三节 繁花与轻愁
第四节 素心绘色
第五节 饭稻羹莼
第七章 悯农
第一节 穷年忧黎元
第二节 唯歌生民病
第三节 一株青苗,两派党争
第八章 别趣
第一节 纸上田园
第二节 十丈篱笆千树竹
主要参考文献
跋
《见南山:田园诗史话》
蔡丹君 著
一部田园诗史,就是一部中国士人的精神史
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无不入诗
田园中的一枝一叶,一鸟一虫,
承载了几千年的诗意起兴
北朝别开生面的散文著作3
敕勒歌与爬山调
阎克敏
爬山调,也称爬山歌,是流行于阴山地区的一种民歌表现形式。关于爬山调产生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是清代中期放垦土地后,晋、冀、鲁、陕等地汉民迁入塞外后和当地驻牧少数民族结合产生的新的文艺表现形式,时间在18世纪中叶,距今约二百多年。爬山调究竟源于何时,史书中未见记载,但其源远流长则是毋庸置疑的。
远在春秋时期,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古典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了啸歌的记载。"啸",《辞源》的解释是"嘬口出声",《辞海》的解释更为形象和具体:"撮口发出长而清越的声音。"《世说新语·栖逸》载:"阮步兵(阮籍)啸闻数百步。"《晋书·阮籍传》:"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阮籍为竹林七贤之首,其啸声可达数百步;孙登为西晋著名隐士,其在苏门山上长啸,半山犹闻,声如鸾凤之鸣,声遏行云,响震山谷,确非寻常之啸,连名重天下的阮籍也自愧弗如。啸之声,悠长、清越、高亢,是无词之长调也。《辞海》说:"合乐为歌",啸和歌总是相伴相生的,事实上长调也总不能一直有调而无词,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更有效的抒发胸中的喜怒哀乐、真情实感。故《诗·召南·将有汜》云:"其啸也歌",《诗·小雅·白华》云:"啸歌伤怀,念彼硕人。"在《诗经》三百篇中,国风为其精华部分,国风即是周朝及卫、郑、魏、秦等十五国之民歌也。其时,阴山地区尚处在猃狁族控制下,属化为蛮荒之地,即便有啸歌之作,也无法编入《诗经》中。但北方民族中不乏民歌的创作和传唱,《十道志》载西汉时《匈奴歌》曰:"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即是明证。
从商周时的猃狁开始,匈奴、乌桓、鲜卑、敕勒、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先后相继在阴山这个历史大舞台上演一幕幕悲喜剧,各民族文化艺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尤其是北朝时期,阴山地区各民族经过长期激烈的战争洗礼终于完成了民族大融合,北朝文化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北朝文化的最精彩部分当属北朝民歌,北朝民歌中叙事民歌代表作为《木兰辞》,抒情民歌代表作为《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两首民歌的原创作者已不可考。这首《敕勒歌》是由东魏大将斛律金演唱后记入史书得以流传的。《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可知这是一篇由鲜卑语译为汉语的翻译作品,是土生土长的敕勒族民歌,是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前阴山地区牧人的放歌。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评价此歌曰:"莽莽而来,自然高古。汉人遗响也。"这样的天籁之作,可惜的是如今我们只能从书本上读到它优美的歌辞,再也无法欣赏到它自然高古、令人神往的曲调,这真是一件令后来人难以释怀的憾事。但我们有理由认为:《敕勒歌》是爬山调的滥觞、爬山调是《敕勒歌》的遗响。
首先,《敕勒歌》诞生,传唱在阴山地区,而爬山调的流行地域主要在阴山地区,二者有地域上的一致性。其次,《敕勒歌》的歌词两句为一节,每两句押同一韵部,第一节韵脚为下、野(古音读yǎ),同属上声二十一祃部;第二节韵脚为茫、羊,同属下平声七阳部。而爬山调也是讲究两句一节、合辙押韵,二者具有音韵上的一致性。古老的《敕勒歌》在句中加上衬字用爬山调来演唱当是一件贯古通今、别开生面的雅事。再则,《敕勒歌》和爬山调就其内容来看,均来源于现实生产生活,反过来用歌和调来反映现实生产生活。
当代学者评述南北朝民歌特点时,认为南朝民歌轻艳绮丽、委婉缠绵,一如江南少女,多情而温柔。北朝民歌粗犷雄放、刚劲有力,恰似塞北健儿,勇悍率真,豪爽坦直。这种说法形象、中肯,很有见地。公元546年,当斛律金为战败了的东魏军高唱《敕勒歌》时,歌声牵动了将士们对故乡阴山敕勒川的思念,激发了他们为故乡而战的斗志,军心为之重振。能使军心振作的歌声必然是雄壮豪放、激扬刚健之声。而阴山地区爬山调,恰恰又继承了北朝民歌的这些特点。
雄伟磅礴的阴山,浩瀚广袤的草原,满眼是壮阔空旷的大自然,满口是粗豪奔放的曲调,这就是北方塞外阴山地区特有的地域特色和特有的地域特色成就了的特有的民歌民调。这是大自然的特别赐予,也是人类文明的薪火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