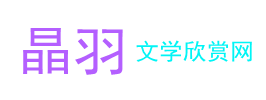上世纪关于牛的故事有哪些
从濒临灭绝到存栏量600多头,来看“上海水牛”的故事,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上观新闻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上世纪关于牛的故事有哪些1
上海水牛是国内公认的著名良种水牛之一。调查统计显示,目前,上海全市有上海水牛饲养户约51家,存栏量共约600多头,90%以上在崇明,崇明也是上海水牛最大的保种基地。崇明区新闻办介绍,近年来,为维持生物多样性,崇明全力推进上海水牛抢救性保护行动,广泛收集崇明农户养殖的牛群信息,开展基础数据登记工作。滩涂中放牧,稻田里耕作……一起来看上海水牛的故事↓
芦苇间
七月炎夏的晌午,一群水牛正在崇明北岸的一处滩涂避暑纳凉。芦苇边的水沟中,1只母牛和5只小牛犊正在“泡澡”。据介绍,水牛皮厚、汗腺极不发达,热天需要浸水散热,故得名水牛。气温只要超过35度,牛基本就要待在水里。
泡在水中有个好处是防止昆虫叮咬,这就出现了“牛背鹭”的奇妙场景。远远望去,一只只头部和颈部带有橙黄色饰羽的鹭鸟,停在牛背上,悠然自得。这些戴着“黄围巾”的“神仙伴侣”就是牛背鹭,又名黄头鹭、放牛郎,是唯一不食鱼而以昆虫为主食的鹭类,也捕食蜘蛛、蚂蟥等其他小动物。它们与水牛形成了依附关系,常在牛背上歇息、捕食昆虫,故得此名。
中国其他地区成年水牛体重一般为500-650公斤,崇明的品种显然大了一些。这是因为崇明有滩涂、湿地、芦苇荡、密布的小河,这些都是水牛们的最爱。且崇明东部的滩涂是咸淡水交汇处,水、植物中富含矿物质,水牛吃得也好。
牛棚内
上海水牛曾一度濒临灭绝。2016年11月农业部印发的《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十三五”规划》中称上海水牛已绝种。2019年,市农业农村委在调研中了解到,沪郊还有少量上海水牛饲养,便组织摸底排查,某次考察中,在崇明岛、横沙岛遇见少量上海水牛。
中国农业大学畜禽育种国家工程实验室也几次来到上海,对现有的水牛样本作血样采集,再与其他品种的作遗传聚类分析,发现除了崇明之外,来自松江、奉贤、嘉定、青浦等区域的水牛,遗传背景来源全部一致,说明这些水牛都是上海的本地物种。由此,“上海早就没有水牛了”这一说法被推翻。
2021年1月,由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年版)》,将上海水牛列入“地方水牛”品种,关于上海水牛保护性认定的说法终于尘埃落定。
崇明是上海水牛名副其实的原产地之一,保种工作责无旁贷。近三年,崇明老杜集团陆续将散放在民间养殖的上海水牛收购回农场,至今,已经陆续收购了160多头。在市、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技术人员指导下,农场为这些水牛“建档立卡”,进行身份编号。档案记录详细,包括养殖地、畜主姓名、毛色特征、出生日期、登记日期等都逐一明确。统一的牛棚管理,对上海水牛的保种研究起到关键作用。
新建的牛棚舒适又科学。按照保种的规范要求,农场在占地2000多亩的区域中规划出适合上海水牛养殖的200余亩场地(包括辅助设施),建立水牛保种场及牧草种植基地。基地内配套新建了水牛粪便沼气处理设施、废弃物堆肥处理中心,杜绝养殖产生的排污污染,将粪污资源化利用做到最好标准,用以改善土壤肥力,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从而带动各类作物循环种植,打造种养结合生态循环模式。
田野里
自古以来,水牛便与农耕紧密相连。崇明是农业大区,大规模机械化之前离不开水牛。上海水牛1岁半即可进行调教使役,一般2-3天就能学会耕地;成年牛一般每天可使役8小时,可耕水田4-6亩、旱地6-8亩,最高可耕10亩,犁地深度14-20厘米。简单来说,1头水牛可顶20个精壮劳动力。
滩涂中放牧,稻田里耕作,便是这里水牛的归宿。在滩涂上,牛与鸟类和睦共处。鸟在牛背上为它清理寄生虫,牛的排泄物是植物的好养料。在崇明的许多散田、小田,机械不便进入,直至今日人们还是使用水牛耕种。
上世纪关于牛的故事有哪些2
五十多年前的记忆:狼出没
文 | 吕自学
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处于百废待兴时期,农村也非常落后。老家村子周边沟壑纵横,蒿草纵生,狼、狐狸、野兔、黄鼠狼等各种动物在村子周围时常出没。白天它们都隐藏在沟壑、蒿草中。到了晚间,村子各巷城门一关,城墙外就是一个动物的世界。
匪扰、狼患,阴森、恐怖,笼罩着整个村庄。国家先剿匪,给老百姓一个安宁的日子。从那时起,没有土匪了,城门打开了,但狼患还时有发生。那时候,“狼叼娃”的奇葩事,狼吃羊、狼吃猪的事也屡见不鲜。黄鼠狼吃鸡,那是小事一桩,不是你家,就是他家,早上主人打开鸡窝,几只鸡一动不动。还不是一只,每次都是几只。
老家村子东边的关帝庙里,经常有一对要饭的夫妻,隔三差五地住在庙里,那男的村里人都叫他凉娃,女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们是两个逃荒要饭的外地人。夜晚在庙里避难时,一不小心,睡着了,狼把娃叼走了。从那以后,凉娃的媳妇就像鲁迅先生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一样,疯疯癫癫的天天在附近村子里转悠,她的丈夫凉娃跟在后边,挨家挨户地找,像喊“阿毛”一样喊着她娃的名字,见人就问看到她娃了没有,很是凄惨。村里人看着他们着实可怜,就把家里剩下的饭、馍送到庙里,让两个可怜的人不能再饿肚子。
也就在那个时段里,我们村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名叫四娃,长得身材魁梧、人高马大,他没有父母,吃百家饭长大,家家有事他都去帮忙。有一年夏天,天气炎热,村子四周都是城墙,凉风进不来,到了晚上,喝了以后(老家把吃晚饭叫“喝”),大人带着自己的孩子,拿着凉席,去城外的场面子歇凉,等夜深了,气温凉了,大人就叫醒孩子回家睡去了。四娃是一个人睡着了,且他睡的地方是院场边,夜深人静,天又黑,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到了半夜三更,狼来了,狼咬住了他的脖子,他憋醒了,求生的欲望使他铆足了劲,两只手抓住狼嘴猛掰,十八九岁的他,年轻力壮,据他给村里人说,狼嘴掰扯了,嗥叫一声后,转过头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自从狼咬脖子以后,给四娃留下了后遗症,一张口说话,喉咙就发出打嗝一样的声音。在我离开家乡以后再次探家,还遇到过他,和他谝过闲传,聊过狼咬脖子的事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村的作家雷道平还把这件事写在他的小说里了。
我自己和狼也有过两次相撞。
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堂哥要结婚,老屋里实在住不下我们一家五口人,父母亲在亲朋邻里的帮助下,先在邻居家住了一半年,又历经千辛万苦、省吃俭用,终于在村子的外边盖了几间单面厦房。整个村子,除过生产队的场房、饲养室以外,就我们独独的一户人家。当时,正值寒冬季节,院子没有来得及打围墙,也没有安门,只用栅栏从里面顶住,到了晚上,寒风呼啸,狼嗥狗叫,十分凄凉。第二年的秋季,生产队从河南收购了一批“南瓜”猪,是把猪装在麻袋里从河南运回来的,到村子后,像倒南瓜一样把猪倒在地上让社员们挑选购买。所以,当时大人们都把这批猪叫做南瓜猪。听大人们说,猪的价钱是五毛钱一只,我们家挑了三只比较欢实的就买下了。
喂了一段时间后,小猪也熟悉了环境,每天早出晚归(那时是散养),时间观念特强,十分的可爱。
就在深秋的一个傍晚,三只小猪回来了两只,母亲就让我去寻找。我出了家门后,天已经快黑了。记得那时苞谷基本掰完了,但苞谷秆还没有割掉。我从城东找到城北,在苞谷地里一边寻着,一边叫着。这时候天已经漆黑一片,苞谷地里有各种声音传来。虽然我在同龄孩子中胆子是比较大的,但胆怯感还是袭上心头,就赶快往回走。因为两边都是苞谷地,走着走着,总觉得后边有什么东西跟着我。我怕极了,但就是不敢回头看。当我距生产队饲养室有五十多米的时候猛然回头一看,两束蓝光直射着我,距离就是十来米,我声嘶力竭地大喊:“狼,狼!”我伯父是生产队的饲养员,这时候他正给牛拌草料,听到外边喊狼的惊叫声后,随手拿着拌草棍冲了出来。我在惊魂失魄中抱紧伯父,当我们回望的时候,那两束蓝光还在和我们对峙,伯父抡起拌草棍,大吼一声:“还不走!”这时候两束蓝光像小车拐弯一样,调转头悻悻地离开我们的视线消失在夜幕中。
转眼间到了1967年,狼在村子周围还时常出没。早晨起得早的老人去地里犁地,多次捡到狼没有吃完的残缺不全的猪和羊。放羊的人眼看着狼把羊羔叼走的事也时有发生。也就是那年的春天,大队在村子西南修一条引水渠,要把山下洪水河里的水引下来浇地,每个生产队按人口分一段工程。开工以后,工地现场就自然形成了一条舞动的长龙,在那“男女老少齐动员”的年代,工地上红旗飘飘、锣鼓喧天,十分热闹。
修渠所需要的石料,由各生产队抽调的石匠统一从罗敷河东边的石材场采供。石材场的附近有一片生产大队的林场,驻场老人经常和石匠们谝闲传。一天,林场老人告诉石匠们:“最近几天晚上,这里经常有狼嚎声!”石匠队伍里,有我们生产队的一名社员叫郑五十,他和我叔父关系好,在老家按辈分我叫他五十叔,此人不但是一位破石头的好手,还爱好狩猎,家里狩猎所需“武器”,样样俱全。冬天下雪后,扛上猎枪带上狗撵兔是他的强项。在没有动物保护意识的年代,在农闲时节也经常和我叔父上村南的秦岭深山打猎。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每次都有收获。我吃肉最多的是香獐肉,麝香他们卖给药铺,肉大家吃。五十叔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二天早上出工,就把他家一个据说有十五斤重的铁夾子带到工地。收工的时候,他把铁夹下在狼常嗥叫的那片区域的一丛小树林里,并用粗麻绳固定在一棵碗口粗的树上,听说饵是从杀猪匠那里要的猪下水。
第二天早上,五十叔就和往常一样,早早地去了工地。他先去了他下铁夹的地方,到那一看,傻眼了,铁夹不见了,麻绳断了,树下有点点血迹,草丛、树叶被爪蹄踩踏得一片狼藉。这时候石匠们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工地,他们分头在附近搜寻。十几分钟后,有一人刚刚进入一片坟地,正准备踏进一灌木丛时,前边的坟包一干草堆发出了响声,这个石匠抬头一看就连声喊道:“狼……狼……狼!”
这时候,正是工地出工的时间,在一片“狼,狼,狼”的吆喝声中,开始了人追狼的“战斗”。这时候的人们没有一点胆怯感,手持铁锨、镢头、撬杠、钢钎,一个个勇往直前,狼在前边跑,人在后边追,狼停下来了,人也停下来了,狼走了,人又继续撵,就这样持续了两三个小时。由于狼的前腿被铁夹夹着,就像戴着脚镣的囚犯,艰难地前行着。大概到了上午十点多或十一点的时候,狼实在是累了,跑不动了,硬挤钻进了只能容下身子,尾巴还在外面的石条下边(农村地里拉架子车的小路上的小桥,为了过水,上边铺两块石条)。人们用钢钎从两块石缝往下戳,在确定狼再没有任何反抗力的时候,把狼从石条下拖了出来。狼的头部有一个大窟窿,一呼吸,血从窟窿里往出冒,但是不能动了。就这样延续几个小时后,才停止了呼吸。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宰狼的时候是在生产队的场面子里。当时大人、小孩围了好多人看热闹。在现场外围大约一百多米的距离外,有好多狗对着宰狼的位置狂吠,就是不敢越雷池半步,狗的主人把狗往宰狼的地方拽,狗挣扎着死活不挪步。我巷里一条平常很凶猛的“赛虎”也是如此。这也是我第一次发现的、且亲眼看到的情形。
据大人们讲,狗是怕狼的,马、驴、骡子都怕狼,尤其是驴和骡子,见到狼后,就跪下,躺倒,任由狼的撕咬吞噬。最不怕狼的当属两岁多的牛犊,它用犄角与狼去战斗,追得狼满地跑,最后狼以失败者逃之夭夭。牛犊以战胜者的姿态凯旋,昂首阔步来到主人的面前,等待主人的褒赏。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听大人们说最顺从的是猪,猪看到狼后一动不动,任由狼的摆布。狼用嘴轻轻地咬住猪的耳朵,用尾巴扑打着猪的屁股,吆喝着离开猪舍,到了野外没人的地方,开始享受美味佳肴。这一切,我都是耳闻,没有目睹。
时光到了1976年,这时候的我当兵离开家乡已经七年有余,历经磨炼,已经成长为一名部队干部。部队驻地是陕西一个小县城,且是秦岭与巴山深处最偏远的地方,一边靠四川,一边靠甘肃。在七十年代初期,可以说既偏远,又落后。落后的程度就不再赘述,大家可想而知。
部队营房在县城的最东边,营房的西边是县城的主街道,也是该县的政治文化中心。政府机构,公检法都在那一块,即便如此,一天到晚还是那么冷清,犹如平川县的小镇。
营房门朝北,往东走,紧靠连队菜地是一条南北走向、且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路的下边,农舍、农田,再往前不到二三百米就是一条绕城河,平常河水不大,踩着几块石头,蹦蹦跳跳就过去了,过河就是几户人家,山地、山坡连成一片,最高处当地人叫东山观。这一片的地形地貌,我们再熟悉不过了。部队每年的射击,夜间射击、山地射击、投弹等科目的训练,都在那一块进行。每天下午还要去河坝里拉水,星期天还要到附近的生产队学雷锋、做好事,农忙时还要帮农民收麦子、收稻子。对那一块地方可以说了如指掌。
有一天早上部队出操回来后,一位班长在洗漱的时候告诉我:“指导员,最近几天晚上两点以后,我上哨时听到东山观下边有狼叫。”我随口便道;“再听到的话,把我喊一下。”那时候的我还是单身,虽然是干部,单间宿舍,但白天晚上,房子门从来没有关闭过。那时人确实单纯,一天到晚和战士们摸爬滚打,真正地打成一片。
隔了两天的一个晚上,我在睡梦中,被班长推醒:“指导员,这会儿狼一直在叫。”我翻身起床从班里提了一支冲锋枪装上一个实弹夹,还有两位班长刚刚下哨,三个人带了三支冲锋枪离开营房。这时候夜深人静,狼还在嗥,听起来特别的阴森。我们轻轻地往前走,天气晴朗难得一见的月光洒满大地。我们过河后,我停靠在一个坟头的树下,让他们两个分头从两侧往我这边赶,因为西面是县城,狼逃跑时必须经过此地。
我调整好自己的位置,身体和树贴得很紧很紧,好像成了一颗有眼睛的树目视着前方,环视着两侧。我的身后是一断面山体,河水从我左侧转弯向西流动,快到县城边沿时,又顺山体向南奔流,我所在的位置是狼“回家”的必经之路,地形对我十分有利。大概十几分钟后,我的正前方突然出现两束亮光,这是我十分熟悉的光影。在月光下,虽然没有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间那么蓝色发光,但还是炯炯有神,这两束蓝灯在身体的作用下,一蹦一跳地向前移动。在夜间,人的双目在狼的眼睛里是什么颜色、什么状态,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狼与我们同时都发现了对方。也可能是两位班长的动静惊动了狼,也就是在这一瞬间,在树的掩护下,我轻轻地举起冲锋枪,狼也迅速调转方向避开我,绕道下河堤向西蹚水过河,然后再左转向南跑后再次过河,我喊着他们两个赶快下来,同时转身走截路,由于是夜间,狼的灵敏度、速度太快了,我到预设位置时,狼已经到了河的中间,并踏着浪花迅速上岸。山体遮住了月光,距离虽然在有效射程以内,但由于是深夜、况且目标在运动的状态下,即使我进行过夜间射击训练,也望之莫及,在无望的情况下,我朝着狼奔河堤的影子,打了一个点射………狼消失在夜幕中,向后山的方向逃去。我们三人会合后,回到了营房。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狼的嚎叫声,连狼的影子也没有见过。现在回想起来,感觉人确实有点残忍。狼在夜间嚎叫,它可能在呼唤着什么,或者有什么诉求,人类不得而知,人类却追杀它。这可能和社会环境有一定的联系,社会还停留在“狼吃娃”的那个时期,对狼的原罪还没有从心底涤除。
人类的文明进步需要有一个过程,生态文明、人和动物和谐共生,共建生命共同体,已经成为人类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因为,在地球上生存,不只是人类的专属权,动物们也有在地球生存的权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由于是五十多年前的记忆,如有与当事人以及真实事件有出入的地方或用语欠妥之处,请谅解。)
作者吕自学,陕西华阴兴乐坊村人,1951年10月出生,1969年2月入伍,1989年9月转业,陕西省汉中监狱退休干部。上班忙工作,退休成了“闲人”后,看闲书、写闲文是退休生活的最爱。曾发表散文十余篇。
END
图片来源:网络
责 编 | 王越美
审 核 | 吴汉兴
▼
上世纪关于牛的故事有哪些3
一天有三头牛正在吃草
突然,有牛说专家来了
三头牛撒腿就跑
等到了
安全地带
一脸懵逼的母牛
说你们跑啥?专家吹牛逼
我就跑了
惊魂未定的公牛说
专家不仅吹牛逼
还扯蛋
母牛听了以后
看了公牛一眼
两头牛同时看着那只
未成年小牛
你跑啥啊
小牛得得瑟瑟的说
我听说专家不仅吹牛逼,扯蛋,
还扯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