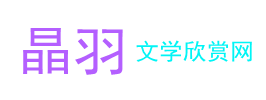有自然隐喻的故事
重新被打量的“自然”,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有自然隐喻的故事1
作者:李 浩
《自然课》《谈谈鸟儿》《青头鸭》《紫水鸡》《有关洪湖的野生动物及其他》……我猜测,诗人哨兵在《在自然这边》这本书写洪湖和自然的新诗集中“暗藏野心”:一种是博物志的野心,他充分利用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熟稔,为故乡真情抒写;一种是建立个人地域性标识的野心,他希望自己的写作能为这片土地确立属于它的文学位置;一种是“百科全书式”容量的野心,他试图将个人、自然、生活、历史、文化等尽可能多地纳入这本书中。更为可贵的还在于,他的这本书有重述自然、重铸诗歌的“自然”书写的野心,甚至可能是,先是有了这种追求,才有了这本《在自然这边》。
我如此猜度的根据,源于反复的阅读。在《在自然这边》的“自序”中,他略显急迫甚至带点小傲慢地向我们承认,他这部诗集,与“找到‘自然’,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传统有关”,与现代化进程中“自然”的变化和他对新诗可能的思考与探寻有关。是的,他试图接续传统,将属于现在、现实和当下的一切“纳入”自己的诗中,为其注入新颖、别致和统一性的诗意。
基于他的种种“野心”,使得《在自然这边》有一个整体性、总括性的思考,呈现的是一个“建筑群落”的面貌,而每一篇又能各美其美,显现异彩。诗集中的作品既有简洁的一面,又有浑浊的一面,既有单一向度的发力,又不乏繁复和深邃。在诗歌创作中,有“野心”是可贵的,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哨兵极有才华地实现了他的“野心”。
比如这首《向莲花及斑嘴鸭和护鸟人借宿》——
鸟儿让我哀恸。那只斑嘴鸭拖拽断翅
天黑时,又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躺在莲花底下时,护鸟人
绕着野荷荡,一直都在呼唤
那只鸟儿。这种声音
贴着洪湖传来,听起来
却来自世外,是虚无
在寻找虚无,空寂在寻找
空寂。躺在莲花底下后
每到护鸟人叫一下,斑嘴鸭
应一声,莲花就会落一瓣……
我认为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它描述自然和自然事物,但不是习惯性赞美和隐喻性抒怀,而是将审视、事实和个人悲悯强力接入。自然事物一方面依然是自然事物,另一方面,又变成了审视、想象、思考和追问的对象与载体,诗人在保护自然事物具体属性的同时又使它呈现为载体和容器,让二者相得益彰。第二,将叙事性纳入到自然书写中,在让它有了故事感的同时又凸显“我”的存在。“我”介入到自然和事件中,强化了个人性,也让“我”对自然事物更加“感同身受”。在中国诗歌传统中,自然要么是一种背景性存在,要么是造境中的“客观事物”,尽可能消弭个人的主观性,即使偶有强化也多止于“孤句”,是跳跃性的存在;而在哨兵这里,“我”的在场感和亲历性同时获得了强化。第三,悲悯性。我们以往的“自然”书写往往至“感怀”和“睹物思人”为止,但哨兵真正站在了自然的一边。那些自如的、自由的或是受伤的鸟兽虫鱼,诗人悲它们之悲、喜它们之喜、哀它们之哀、痛它们之痛……在这首《向莲花及斑嘴鸭和护鸟人借宿》中,哨兵的这一倾向显得足够清晰、真切。他将自己的悲悯注入受伤的斑嘴鸭身上,甚至让它的疼痛发出让人心碎的颤音:“每到护鸟人叫一下,斑嘴鸭/应一声,莲花就会落一瓣……”
我还将哨兵的这部诗集看作是对“洪湖”的一次次复写和复拓,他书写着洪湖的不同侧面、不同向度,在一次次的复写中,“洪湖”的水面被缓缓抬高,并且“生出”了涡流和浮游于水中的生物。每一首诗,是独立的结晶体,而如果将它们放在一起,便产生更为宏阔的统一感,呈现出在不断解读和抚摸中完整起来的“象身”,属于“洪湖”的——不,不只是属于洪湖的,它甚至令人惊艳地呈现了“百科全书”的性质,至少是一部区域史志。
诗人、小说家博尔赫斯有篇小说《创造者》,写一个野心勃勃的创造者,试图按照真实比例画下一幅世界地图。为此,他耗尽了一生的精力。而等他将这张“真实”的世界地图完成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画下的,竟是自己的那张脸。我一直将它看作是关于诗歌写作的经典隐喻,而在哨兵的诗集《在自然这边》中,我再次想到了它,因为它在某种意味上也是一种验证,验证哨兵在殚精竭虑的自然书写中,本质上画下的是自己的那张脸,是他个人精神向度的整体凸显。
阅读哨兵的《在自然这边》,我还发现其中一个极有意味的注入。譬如《古桑》《湖边休闲庄》《水雉》等诗,在并不刻意的自由联想中,我会想起《洪湖赤卫队》,那部有些淡忘了的电影中的歌曲。我当然能够意识到哨兵在诗中的牵挂,也能意识到,那样一种“境遇”为哨兵“成为自己”着色多多。我还发现,哨兵诗歌中某些词语的使用是“重”的,他有意强化语词的强度和张力,不肯略有平缓,而这些词往往又有种笃定的、斩钉截铁的性质。是故,阅读他的诗歌往往会遭遇小“颠簸”,它不肯顺滑而平庸,不肯像水一样倾泻着流淌,这是哨兵诗歌的个性之处,也是他诗歌的动人和耐人寻味之处。甚至可以说,他就是通过这样的“超过世界三倍重量”的诗句,为我们以为的熟悉重新命名,部分地,也建立起了深邃。
(作者系河北师大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有自然隐喻的故事2
2022年元旦那天,看着报道,中国GDP已经突破100万亿,稳居世界第二,占整个世界GDP的比重达到17%。国人创造财富数量和速度,令世人称奇。
想起半个世纪前中国的贫穷落后,似乎有种幻如隔世的感觉。
我们居住的这块土地,还是50年以前没有任何区别的土地,地形地貌、自然资源、甚至居住的那些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以前我们不仅创造不了任何财富,甚至连吃饭、生存都成了问题,而现在为什么都市高楼林立,乡村富饶美丽,到处呈现出百姓富足的景象?
反复思考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人和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脑子里的思想变了。
50年前,你做生意,叫投机倒把,是犯罪行为,要判刑的,现在你做生意,叫创业,叫企业家;
50年前,你学习知识,叫臭老九,在所有工农兵等职业排行中最低级,你搞学问,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现在,你学习知识,叫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你搞科研成专家,叫科技领军人才。
50年前,整个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奉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我们提出市场经济、法治社会,高举“共同富裕”的旗帜。
由此可见,今天中国的巨变和走向富强之路,其最初的起点,就是80年代改革之初,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潮之下,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大转变。因为思想观念改变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潜力被激发出来。
按照这个思考方式和历史变革的逻辑,如果要看到更为美好的未来社会,看到更加强大富足的未来中国,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是不是还要进一步变革呢?或者说持续解放思想呢?
更甚者,我们又如何能够清醒地感知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是解放思想的某些观念,实际上已经慢慢成为陈旧的思维框架,而且开始束缚我们进一步创新变革了?
由此,明君想起了两个神奇的故事。
故事一,某个部落山寨自祖先开始,一直流行一种习俗,某户人家只要家里有人去世了,就要请整个寨子里的人参加葬礼,葬礼要持续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时间每天都要请寨子里的人吃最好的饭菜。于是这户人家要把自己家养的牛羊都宰杀了招待全寨子的人,还要借20多万巨债才能把葬礼办完。等葬事办完后,这户人家需要辛苦劳作二、三十年才能把债还清,然后就会发生另一个亲属的去世,于是这种“举行葬礼”、”背负巨债“、”“几十年辛劳还债”的模式再一次重复循环,寨子里个人一生、家庭持续,如此循环往复。
对于这样的部落山寨,如果他们不改变如此风俗习惯,彻底抛弃这样顽固的思维模式,人和家庭的富裕和发展几乎不可能。
在此申明一下,从内心而言,明君根本不愿意用如此低劣的故事,而且肯定会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推论出所谓“心怀歹意”的恶劣隐喻。明君选择这个故事的唯一原因是,再也没有那个故事更能鲜明、典型地揭示,传统习俗观念的束缚对个人、家庭和社会进步的阻碍了。
故事二。一位老爷爷带着自己的孙子在山区旅行,他们来到一个农场休息,看到农场主正在喂鸡。小孙子发现,在这群吃食的鸡中,有一只“鹰“也在耷拉着翅膀吃食。小孙子很好奇,就问农场主,你怎么把一只鹰与鸡养在一起,而且它怎么不飞走呢?农场主说,这只鹰很小的时候,从鹰巢里掉下来,他发现后带回家就和鸡一起养着,随着这只小鹰慢慢长大,它只能模仿周围鸡的行为,走路奔跑吃食,它也认为自己就是一只鸡了。它无法觉察到自己是一只可以翱翔天空的鹰,也不会尝试飞翔。
小孙子央求爷爷从农场主那里买下了这只鹰,他们把它抛向天空,但这只鹰还是翅膀震颤了几下掉落到地上。爷爷带着孙子爬到山顶悬崖之上,然后再把这只鹰抛向悬崖,鹰震颤着翅膀不断地滑落,就在即将落入谷底之时刻,这只鹰终于发现了自己翅膀的力量,奋力展翅高飞,冲上蓝天,去寻找鹰群去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也许我们是被传统当成”鸡“来养着,尽管可以从传统中获取很多食物与营养,也过得很舒服,我们始终无法突破传统的旧观念,无法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一只”鹰“呢?
故事中这只鹰,只有在快落下万丈悬崖的危机时刻,才挣扎、觉醒,重新认识了”自我“,觉悟了自己作为”鹰“的真实本性,这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
也许大家都听说过这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表明,过去流传下来、似乎约定俗成、每个人出生以来就默认的、固有观念习俗,如何严重地阻碍个人、家庭、社会的进步和繁荣。第二个故事说明,一个人要在行为上产生飞跃性突破,必须重新认识自我、定义自我,经历对自我身份认识从”鸡“向”鹰“的觉醒。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中国人已经走出了过去思想的”寨子“,而且越来越觉醒到自己”鹰“的身份。
可是,我们又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我们的脚步会不会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踏入另一个”寨子“,或者轻慢地来到一群鸡中,享受投养食物的舒坦与满足?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未来发展和持续富强的保证,就是必须具有自我革命的精神。自我革命的启动和成效,首先需要在认知上持续突破固有思维框架,对自我进行重新再认识。
也许再经历半个世纪之后,人们还会说,一样的山河一样的人,因为思想观念变了,这个世界也就变了,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顶尖国家。
行文至此,明君要道出写此文的目的了。接下来在2022年,明君将以搬砖的心态,努力以零零碎碎的所谓”新观念“、”新视角“,写10-20篇文章。
以”愿做事、要想事、不惹事“的行为原则,以正面、建设之心态,生产一点”文“砖”字“瓦,如尚能为未来宏宇大厦建设之所用,乃为幸事也。
由于每篇文章的主题或者学术探索的性质,故只在公众号中以说明的方式,解释文章的题目、研究问题与立意,主题内容将不在公众号里发出来。
我已经建立了”君言君议“微信群,10-20篇文章主题内容只在这个群里发表。想阅读文章的朋友,看到我对每篇文章的题目、研究问题、立意的解释后,如果感兴趣,可以私信给我,等我评估、核定后邀请入群,即可阅读。
是为稳妥之举,请各位看官谅解。本公众号还会继续发表有关商业、社会热点之文章。
有自然隐喻的故事3
Spring
《春山谣》颇有几分“道法自然”的意味。这里的“自然”,既是写实的、也是隐喻的。小说中大部分的内容,都关乎人对土地和森林的重新接近,人要在缓慢的、质朴的、近乎前现代式的自然环境中,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存。
新批评
·文/李壮 ·
《春山谣》是一部好看而不好谈的小说。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张柠先生对待广大读者是友善的(小说的叙事舒缓流畅、细节也鲜活丰满),对待小说人物是温柔的(顾秋林和陆伊们的命运固然泥泞、却永远不失盼望),对待摩拳擦掌的评论者们,却多少有些无情——我们似乎很难从小说中找到确凿的“关键词抓手”,借以去攀登并开凿那些熟稔而宏大的阐释。抓手并非没有,但往往显得可疑:这部作品写到了“历史”,然而并未专究;写到了“苦难”,然而并未痛陈;写到了“人性”,然而既不赤裸也不极端……说到底,《春山谣》只是写了一群年轻人,他们胸中揣着代代相似的火,在一个有些特别的时代、去到一个未曾料想的地方,经历了一段偏离常态的生活。
此事可大可小。可大,指的是“偏离常态”,偏离总有原因,而世间的原因但凡较劲总都可大谈特谈、上纲上线。可小,指的是“经历生活”,生活本是寻常的、也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至于它被归入哪一类人间的指称——在上海逛街或者在江西伐木——或许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那些源自生活的“差别”、却又超越了“差别心”的事物,诸如忍耐,诸如希望,诸如成长,诸如爱。这些永恒的、江海般宏阔的话题,就像有缩骨术或遁地法一样,蛰伏在小小的、寻常的生活体内。《春山谣》的取径是事情“小”的一路。它没有那么多惊心动魄、没有那么多争斗曲折、甚至没有那么多刨根问底,只是把生活的卷轴缓缓打开、只是让年轻的男女哭了又笑来了又走,书脊下悄然沉积的种种,却不可谓不大、不重——这是管中窥豹,是小孔成像式的投射,它通过细窄的不规则的穿孔,把小小的火焰投射成大大的光明。
这样的细致的笔墨和荡漾的情感,使我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乡间风光、也想起中国古典田园诗或民歌里的句子。
在此意义上,《春山谣》颇有几分“道法自然”的意味。这里的“自然”,既是写实的、也是隐喻的。小说中大部分的内容,都关乎人对土地和森林的重新接近,人要在缓慢的、质朴的、近乎前现代式的自然环境中,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存。“自然”在此,是明确的、实体化的对象,它是林场里的乔木、水田里的蚂蟥、空气中弥散的稻花与粪便的气味、是荒山野岭野兔豪猪野鸡鹧鸪。《春山谣》对这样的自然从来不吝笔墨。“大路两边是起伏的山丘。路旁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灌木蓄势待发。水田里的泥巴和野草根茎,在中午的阳光照射下,散发出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这是知青们初到春山岭时的“直观冲击印象”。这样的细致的笔墨和荡漾的情感,使我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乡间风光、也想起中国古典田园诗或民歌里的句子,此类描写借助了知青们的眼睛,进而无疑是知青们内心震颤的投射:“对于陆伊而言,眼前这些景物和人物,此前只是在书本上见过,如今却近在咫尺。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真的像是绘在图画之中一样啊!”
不同于其他很多知青题材小说,《春山谣》没有简单地把那段生活讲述成“激情燃烧的岁月”、同时也并不急于让故事变得苦难深重涕泗横流。对自然——以及紧紧依托自然存在的农耕生活——的细腻感知,在小说中获得了很从容的铺展延续。知青们迅速投入到生产之中,虽然时常遇到小的意外和阻挠(例如被蚂蟥叮咬、不能习惯粪肥、长期吃不到肉食等),但总体上都能够跨越克服。事实上,直到小说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处,知青们的“回归自然之旅”依然总体顺利,他们都还在平静甚至不失热情地操持着辛劳的农村生产生活。甚至我们看到,幽深强大的自然悄悄改变了这些年轻人的性格——在西岭沟无人山洼里待了几个月后,顾秋林“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沉默、强硬、坚定。自然与人的内心形成了对话、并相互浸染,它的强大力量逐渐显现出来;自然不仅仅是外在的对象、也时常作为内化的“我”的一部分而出现,并由此不断接近“青春”与“成长”的故事内核。与此同时,在另一群人眼中,这自然始终是亲切的、抒情的,例如本地的孩子们。与自然有关的愉悦,始终环绕着马欢笑、王力亮及其兄弟姐妹们。自然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诗性的。反诗的是叛离了自然、明显已不再天真的成人世界(父母辈的世界)。
对自然——以及紧紧依托自然存在的农耕生活——的细腻感知,在小说中获得了很从容的铺展延续。
小说里,年轻人们“上山下乡”,形式上是对人造的、充满意识和观念固习的都市文明的逃离,它呈现为一个回归至农耕文明、也即自然世界的梦幻式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这样一种社会实践,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规模地展开,一方面存在着的历史运动的外力因素,另一方面,同样也有知识青年自身的理想主义情结在起作用——倘若说,下乡一事于顾秋林而言还带有某种难以明言的无奈成分,那么陆伊选择投身农村,则属于完全主动的个人选择。有趣的是,这种从人造世界向自然世界的逃逸冲动,本身是人造世界观念高度繁衍增殖的产物。在这些年轻人看来,不直接从事生产劳作是不光彩的,高度精细化的社会分工是具有腐蚀性的,只有亲手种出自己的粮食、亲手盖起自己的房子、在习性乃至样貌上尽可能地与土地同一,这才是英雄的行为——抛开真实历史中的意图背景不谈,至少在现象层面,结构复杂的现代革命话语,同最质朴的古典诗性理想,在这群年轻人开赴乡间的队列中重叠了起来。
然而,这种回归在相当程度上只能是虚幻的。就在此前的引文中,出现了美丽的紫云英。然而,它们是“即将成为绿肥”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在分类学和现实理性的冲击下瓦解了,田园风光固然美丽,但其中的某些风光终究只能被用来沤肥。而肥料无非是帮助庄稼生长,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既然如此,为何又要离开上海到乡下来呢?亲手种出的粮食,同城市里精细分工之下获得的商品粮,究竟又有何本质区别?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一场对历史逻辑的颠覆,依然被强大的历史逻辑以更加隐秘的方式捕获。因此,在小说的后三分之一部分,辛劳、单调、自力更生的乡村生活终于变得难以忍受,“闯进乡下”的青年们,又急切地渴望“逃回城市”。矛盾冲突随之多了起来,有人机关算尽,有人造化捉弄,有人疯了,有人想死。在与城市生活的对照中,自然和乡村生活,逐渐他者化、甚至隐喻化。
无论如何,生活依然在继续,它看起来就像几千年间所习惯的一样正常,所有的难题依然要放在这只筐子里慢慢寻求解决。这是《春山谣》一书的沉稳松弛,是叙事本身的“自然”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反向逃回”的部分中,《春山谣》的叙述也依然是节制、从容甚至松弛的。矛盾很多,冲突不少,但没有出现什么真正的坏人:知青群体中固然有人搞阴谋诡计,但这在我们看来多少有值得同情的成分,甚至阴谋诡计的最终结果也往往是“未能如愿”甚至“适得其反”;负责林场工作的当地干部彭击修,看起来最像是“反派人物”的模子,其实也并不算飞扬跋扈、草菅人命的角色,相反,他其实也是个满腹苦水有情感有悲伤的倒霉蛋。《春山谣》里不乏悲苦,但不特别强调苦难;有人变坏,但很少见完全意义上的恶人;流泪流血,但并不一味地“问责”“控诉”。无论如何,生活依然在继续,它看起来就像几千年间所习惯的一样正常,所有的难题依然要放在这只筐子里慢慢寻求解决。这是《春山谣》一书的沉稳松弛,是叙事本身的“自然”风格。
在这种自然的、平静的叙事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春山林场的生活是苦的,甚至有些记忆还很悲伤,但人性的考验在这里并不明显殊异于其他地方,生命的成长在这里并不比在别处夭折得更多,情感的盛开和淬炼也并不因一时一地的特殊处境而变得有本质不同。在救起试图自杀的陆伊后,顾秋林沉痛地进行了反思:“到底是什么把我们都变成这样了?”幻想中的乌托邦彻底垮塌了。这瓦解或许根源于个体成长和人性深处的某种必然,它只不过是同春山林场特定的、略显极端的历史和现实处境发生了一些化合反应。
发生在春山岭的所有故事,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的故事,不也都与这三件事有关吗?它们是当下、记忆和永恒,或者说,是现实、理想和爱。
回归上海后的十几年中,顾秋林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卖香烟、想陆伊、写诗歌。“那是三件很小的事,但也可以说是三件很大的事。”说到底,发生在春山岭的所有故事,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的故事,不也都与这三件事有关吗?它们是当下、记忆和永恒,或者说,是现实、理想和爱。
又是很多年过去,顾秋林所关心的这三件事情,在时过境迁后的春山岭,借助“纪念馆”的躯壳再次进入我们的视线——虽然,依旧是“有些懂,有些不懂”。甚至,跳出《春山谣》这部小说之外,再是很多年过去,在与顾秋林有密切血缘关系的子辈们的生活中,这三件“可大可小”的事情依然牵引着年轻生命的轨迹起伏与内心潮涌——那是另一个故事,在先前出版的《三城记》中,“80后”青年顾明笛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古老命题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的重新阐释。在王力亮们的记忆中,顾秋林们“神仙一样突然从天而降……几年之后又突然消失无踪”。但是人、但是青春,真的能够突然消失无踪、就像在梦里一样吗?在顾秋林的风琴声里,在《春山谣》诗句的朗诵声中,古老的命题将被再次叩问,一本书将要接续起另外一本。
就像这部小说的题目——《春山谣》,山是恒久的,而春草年年茂盛,然后它们枯黄、它们凋萎,它们重新成为大地的一部分。这是寻常的,是“自然”的。顾秋林们是这寻常中的一部分,甚至那风琴里飞出的谣曲、那些比人活得更久的诗,也终究是山的一部分、是春的一部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然而,当它们被意识到、被写下、被读到和听到,却又注定将非比寻常——并且,注定投射出无限绵延的回响。
稿件编辑:傅小平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摄图网、出版书影
1981·文学报40周年·2021
每天准时与我们遇见的小提示:
邮发代号: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