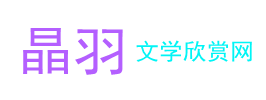关于母亲冻粑的美文
《母亲的冻粑》实属美文!文字朴实流畅,随着冻粑制作过程的徐徐展开,读者已不觉满口生津,向往之至……
凭着精细苛刻的匠心,“母亲”愣是将普普通通的粮食做成了不一样的美食。正是由于冻粑制作费时费功夫,即使后来粮食充裕了,年轻人也不愿意学做冻粑。随着母亲的离世,这种纯手工制作冻粑的工艺也在我们老家失传了……
“三九四九,冻死猪狗”。进入三九四九天气,就意味着要过年了。
记得小时候,每到腊月中旬,母亲就开始忙着准备做冻粑,用来招待和打发拜年的客人。
冻粑是四川的风味小吃。我们家乡柏杨坝历史上隶属四川省奉节县,1952年划归湖北省利川县管辖,所以我们家乡自古就有做冻粑的传统。
与一般米泡粑相比,冻粑的风味独特,看上去晶莹剔透,入口特别滑腻纯美,不用任何添加剂,完全是一种回味悠长的自然清甜,一种带着蜂蜜味道的香甜,一种像米酒那样的酣甜。
冻粑是由粘米、糯米和黄豆按照一定比例掺和做成的的。冻粑不仅制作工艺复杂,制作周期长,而且需要特殊的气候条件才能制作。
母亲将粘米加上适量的黄豆浸泡发胀,用石磨推成浆装在坛子里,再将糯米蒸熟与坛子里的米浆掺和搅拌,然后放在室外冰冻十天半月,每天搅拌一次。冻浆的关键要把握好冻的“度”,冻过了头,就蒸不熟,冻的时间不够,也冻不出冻粑的风味。一直要冻得糯米粒成了溶状,米浆开始鼓泡起烽火眼了,才进行下一道工序。
母亲娘家地名叫田坝,外婆是坝子上做冻粑的行家,母亲从小跟着外婆学到了做冻粑的绝活。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工序,经过母亲做出来的冻粑好吃又好看。记得每年一到做冻粑的季节,湾里的婶娘、嫂子们就来向母亲请教,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她们如何掌握大米和黄豆的掺和比例、米浆冰冻时间、蒸冻粑的火候等等。
现在想起来,做冻粑其实都是那几种粮食的掺和,都是那几道工序,只是母亲要比别人更加精细,更加苛刻一些,真正把它当做手艺来做。
冻粑好不好吃,首先是各种原材料的配比适不适量。粘米的品质不一样,口感不一样,掺和的比例也就不一样。各种糯米的颜色不一样,糯性不一样,配比也自然不一样。还有黄豆,掺多了冻粑容易稀皮,掺少了冻粑不够酥软。这些都是母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经验积累。
冻粑好不好看,就要看米舂得熟不熟(白净)。那些年农村还没有碾米机,要靠木礌子碾米,用石碓窝舂米。我们院子的砂石碓窝,一次只能舂一升多米也就六七斤。我们家碾米、舂米都是我和二弟的活路,一人一把笨重的木槌,像铁匠打铁似地你一下我一下地舂。母亲叮嘱我们要把粘米舂成雪花一样的白净,把糯米舂得亮晶晶的。要把糙米舂成这个样子,必须反复舂三、四道,每一道大约半个多小时。不管我们怎样叫苦喊手疼,母亲规定的这个标准丝毫不能打折扣。正是凭着这种精细苛刻的匠心,母亲愣是将普普通通的粮食做成了不一样的美食。
“大人望种田,细娃望过年”。随着母亲准备冻粑开始,年的味道就渐渐弥漫在老屋里,盼望过年的喜悦也挂在大娃细崽的脸上。我们加工完过年米,又忙着上山捡过年柴。看到柴屋里码得高高的干柴,母亲很满意地说道:“过年的时候,冻粑、汤圆、猪脑壳肉准你们吃个够!”于是,我们一天天掰着手指头数时间,盼望着年快点到来。
腊月二十八,家家蒸冻粑。而我们家蒸冻粑的时间一般要推迟到除夕之夜,可能是母亲觉得大娃细崽吃饱了年夜饭,就减少了对冻粑的消耗。
蒸冻粑是最后一道工序,也是弟兄姐妹们最高兴的时刻。大家围着锅灶忙得团团转,有的往灶门口抱柴,有的往锅里掺水,有的帮着母亲清洗蒸具。我当然还是负责往灶膛里加柴烧火,这样可以借助火光看书。那年代,乡下照明都是煤油灯,煤油凭票限购,一盏煤油灯要管一间屋。晚上看书,我只能经常在灶门口当“火头军”。
一切准备就绪,母亲将竹编的粑粑圈铺在蒸格上,蒙上细布,再把冻米浆舀在一个个粑粑圈内,再放到锅里开始蒸。
冻粑蒸得好不好,“火候”的掌握是有讲究的:火大了急了,冻粑容易裂口;火小了升温慢,冻粑容易蒸成“夹生粑”。记得那一晚我坐在灶门口借着火光看《说岳全传》看入了迷,直到满屋里腾腾雾气弥散着冻粑的香甜味,我还在不断往灶膛里加柴。母亲走进灶屋,没有像平时那样提醒我退柴,而是着急地叫我“退火,退火!”年三十夜忌讳大,退柴似乎有退财的意思。
母亲揭起锅盖,撩开纱布,一排排冻粑在雾气弥漫的灯光下晶莹剔透。围在灶前灶后的弟兄姊妹们一拥而上,不顾烫热的水蒸气,争先恐后伸手就抓。母亲站在灶边,大声呵斥着不准五抢六夺,可是没人顾及母亲的招呼。谁的手伸得最长,母亲就用筷子打谁的手,直到一个个都老实规矩了,母亲才把蒸格边上不饱满或者变了形的冻粑赏给我们,把好看的放进筛子里。
刚出笼的冻粑软嫩细腻,拿在手上颤摇摇的,咬一口满嘴滋润香甜。看着我们一个个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一再招呼我们不要憨吃憨胀,要不,初一早上的汤圆就胀不下去了!
一轮又一轮蒸了大半夜,终于积攒了满满的一簸箕冻粑。第二天还有一道工序就是给冻粑“化妆”。
有一些剪纸手艺的母亲在菜疙兜上面刻了“喜鹊闹梅”等图案,蘸上颜料印在冻粑上,一大簸箕冻粑就像一座晶莹的的冰山,上面盛开着红红绿绿的花儿。
我们老家每年的拜年客人都是由各家轮流做东,集中款待,几家主人客人团聚吃“转转饭”。晚上,大家围着树疙蔸火,一边吃着烤冻粑,一边听演唱民间唱本,或者拉家常,这种亲情真的是其乐融融,格外温馨。在我们小时候的印象中,这是一年中最值得期待,最值得留恋的几天。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几天热闹很快就过去,拜年的客人走了,冻粑也打发完了。 正是由于冻粑制作费时费功夫,即使后来粮食充裕了,年轻人也不愿意学做冻粑。随着母亲的离世,这种纯手工制作冻粑的工艺也在我们老家失传了。
几十年的岁月更替,乡村的一些年俗渐行渐远,老家的年味也越来越淡,可是母亲的冻粑味道却依然回味悠长,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记忆中,时时唤起我的乡愁。
作者简介:孙朝运,男,中共党员,湖北省利川市人。先后在利川广播电台、利川日报社从事编辑记者工作,任过《利川日报》副总编辑。退休后学写文学作品,有40余篇散文、小说等作品散见于各种网络媒体和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