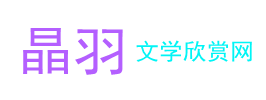关于古蔺大黑洞的美文
故乡的记忆
许华锟
我是四川省古蔺县人。1925年我出生在县城附近的玉田乡田坝头。
古蔺地处四川边陲,与贵州毕节接壤,亦属古称西南彝地。早年受彝族土司统治。原住民为彝、苗、纳西等少数民族。清朝初年“改土归流”(即改土司世袭统治为由政府委派官吏管治),并移汉民入蔺垦殖。我为汉族。幼年曾见家藏族谱记载,我家祖籍在江西,后迁至湖北麻城孝感,然后迁到古蔺。我懂事时,县城里已没有少数民族。他们都在四周山上居住。究竟是汉族把他们赶到山上去的,还是他们就居住在山上,则不得而知了。母亲常讲三月三赶苗场,四周的苗民都要进城来,很热闹。我只隐隐约约记得,似曾和全家的人赶过一次苗场,因人多拥挤,还被人抱着行走,因为太挤了,走不通,就中途折返了。
古蔺四周都是高山,很偏僻。解放前没有公路,不通车。河水流量小,不能行船。食盐、布匹、医药、百货等日用品全靠人肩挑背驼运入。但肩挑得少,背驼得多。用背篼、背架等工具揹运。这也是古蔺山多、道路崎岖狭窄,挑担不如背驼方便之故。我们出外求学,只能走路。
1936年,父亲去泸州川南师范工作,我随他去读川师附小,从古蔺到泸州420里,走了五天。父亲坐一乘滑竿,我年纪小同另一个同学轮换坐一乘,每人走20里,再坐20里。直到上世纪40年代,滇缅路入川了,从叙永到泸州才可搭乘黄鱼车。但从古蔺到叙永仍需走路。
我在叙永上高中,全程140里,走两天。早上出县城,经田坝寨、德耀关、袁家沟。然后就爬山,走约十里的上坡路到箭竹坪。那里有个几十户人家的小场镇。在场上的鸡毛店住宿一晚,第二天再走70里到叙永。有一次,我同大哥同行,到箭竹坪,听说前面地段有土匪出没抢人,因带有学费,便出两个银元,请驻扎在那里的两位自卫队员,护送20里过关。有一年学校放春假。我一个人回古蔺,下决心一天走到家。天刚亮出发,中途除就餐、饮水外,不休息。傍晚走完140里,到家时,两腿已麻木,只能无知觉地机械地移动了。直至建国后,修建了叙蔺公路,才解决了古蔺对外交通问题。
我在古蔺实际生活的时间仅有20年,在重庆生活了70多年。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但重庆给我留下的乡土记忆就不如古蔺那么清晰、亲切而有归属感。我记忆深刻的是这些。
01
我家的那条河
我最留念的是我家的那条河。河不是我家的,但它与我家的距离很近,从家门到河岸不过三、四十米,进出家门都要见到它,同我们家紧密相连。在青少年时期记忆里,总少不了它。所以,我总觉得它就是我家的河。
那是一条古蔺县境内的河流,全长仅100多里。它发源地距我家60多里,从县城侧流过。在县城上下两端分别与两条小河汇合,流经我家门前,而后到太平渡与赤水河合流,在合江流入长江。我家门前这一段河床特别宽阔,约有五、六百米。河水分别从两侧岸下流过,再在下流不远处合拢,中间是铺满鹅卵石的沙洲。河水流量不大,仅十来个立方秒米。大多地段,都可徒步涉水过河,但很少断流。如断流了,我家就在河床中挖一水氹,积存饮用水。夏、秋季河水涨落无常。有被称为涨竹筒水的,来势凶猛。一次,早上,晴天,母亲下河洗菜,发现河水浑浊异常,赶紧上岸,洪水即跟踵而至。她叫我去看时,只见浪头高达三、四米,像墙一样直立着推压过来。几个浪头过后,遂逐渐消落。涨水在沿河冲刷出一些深塘,就成为人们垂钓和游泳的场所。
我家这边的河岸,高约七、八米,上面是人行道,底层是红色沙岩,人们就在延伸出去的岩石上洗衣、洗菜、担饮用水。这里滩浅,也成为我们戏水的地方。这里有一种叫巴壁虎的鱼,黑色,扁平体,五、六公分长。它们常常巴在石头上,流水也冲不走它。我们去捉它时,它不随水逃跑,而是巴着石头转。我们捉到它,就把它贴在鼻子上玩耍。还有一种银白色鳞甲的白甲鱼。夏日骄阳,一群群几寸大的这种鱼,或在乱石滩里翻滚,或一尾接一尾列队似的沿入水岸岩斜坡游走。它们的鳞甲,在阳光照射下,银光闪闪,十分耀眼迷人。在岸上行走,即可见此境况。人们称这种境况为鱼在翻肚了。
有一年涨水,这里冲成一个小塘。三叔用双手托着我的两腋,从滩口冲下,我随着水势,手足胡乱搅动,竟然浮了起来。就这样学会了游泳。先学小浮,即俗称的狗刨烧,然后学大浮,会仰泳。都是老式泳法。我们常游泳的地方是下游二、三百米远的猫儿嘴。这里塘深二、三米,三、四十米宽,一边为岩石岸,岩石上有一株大黄角树,可遮阴。有一个暑假,我随着大哥他们一伙就在这里游泳。每天上午温习一下功课就去游。水温低了,游几圈就上岸晒太阳,暖和了又下水。周身晒得漆黑,背上脱了一层皮。饿了就跑回家,吃茶泡饭下豆豉粑。古蔺的豆豉有一种特别的香味,是地方特产。至今我仍然不时要亲友们带一些来就餐。我的游泳技术不好,并不特别爱好,离开古蔺后,就再也没有到溪河游泳了。
在河里的另一活动就是钓鱼。开初我们像杜甫说的“稚子锤针作钓钩”,用针自己制作钓钩及全套钓具。后来才上街去买鱼钩、鱼线成品。钓竿则一直自己砍竹制作。大哥特别爱钓鱼,有时天麻麻亮就叫起床下河,有时晚上也去。我家附近河段没有大塘,我们钓到的大鱼也就是半斤左右的青钵鱼。前面说到的白甲鱼,不吃诱饵,钓不到。青钵鱼也只有大哥能钓到,我的技术不好,只能钓到黄颡头、石平头和各种小白鱼。有一个夜晚,父亲的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相约去钓鱼,我随他们去猫儿嘴下游几百米远的鱼塘湾钓黄颡头。这里塘深二、三米,对岸边多乱石,黄颡头特别多。这种鱼金黄色、无鳞、扁平头,胸鳍带刺,易伤手。它不偷嘴,见到饵料就大口吞食,有时把钓钩都吞到肚子里去了。浑水夜晚最好钓。人们叫它“憨包鱼”。它个子小,二、三两一条,大的不多。但肉质细嫩鲜美。我们只带了一盏马灯照明。垂钓用下坠子安塘,凭手感的办法。几个大人垂钓,我负责穿蚯蚓、取鱼。仅一个多钟头,就钓了大半盆,全是黄颡头。回到家里,用自家腌制的酸盐菜,煮了一大锅酸鱼汤,美美吃了一顿。
这河段也常有人来用网捕鱼。还有人扛个小舟、挑着鱼鹰来捕鱼,他在水深的地方再放下小舟,登舟放鹰捕鱼。最热闹狠毒的是“闹鱼”。即用石灰、油枯、麻柳叶···等等制成毒液,在深塘的滩口下毒,把鱼闹翻毒死,鱼子、鱼孙都无一幸免。每次“闹鱼”,都有成群结队的人跟随去捡鱼。有一次,我随一批人去下游十几里远的野猪塘“闹鱼”。那里塘很深,两岸都是高山,很阴森。他们下毒后,几斤、十几斤的鱼都在河里翻滚游向浅滩。我胆小不敢下水,只在岸边偷偷捡了几条斤把大的。
那时,这条河的河水清澈见底。随着河段的深浅变换,而现绿色、深绿色、蔚蓝色。鱼翔浅底的情况,随处可见。九十年代我两次回乡,第一次见河水已变为黄色,有异味。古蔺是郎酒产地,全县发展酿酒业,废水就把全河污染了。第二次去,我携四妹从猫儿嘴、经鱼塘湾到石板塘走了一圈。这些深塘都已淤塞、露底。河水虽不黄了,但已成涓涓细流。河床里满布塑料袋卫生纸类垃圾,很恶心。青山虽在,绿水难寻。数年前,听说县政府已在整治,情况有了改善。我想随着十九大提出的建设青山绿水家园精神的贯彻,情况定会变得好于以前。
02
父亲的私塾
父亲名许文彬,字质钧,以教书为业。他上过私塾,也上过新学。私塾是祖父请了一个姓何的秀才,在家里设馆,教他们几弟兄。多年后这个秀才来家里做客时,我见过,一个瘦小的老头。家里人很敬重他,都叫他何老师。听三叔讲,何老师教他们读“四书”、“五经”。易经最难读。何老师根本不细讲,只要求他们背诵。他们不懂得,也很难背得。父亲上的新学,是叙永联中,在这个中学毕业。毕业后做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从我懂事起,知道他开过两次私塾馆。一次在家里,一次在花厅头许家。其后,他随潘从理到泸州川南师范作过职员。不久,抗日战争兴起,他即返蔺与潘从理共同创办勉仁小学。潘任校长,他任教务主任。这是他一生中做的一件有公益性意义的事。不幸的是勉仁小学开学仅数月,他就生病去世了,时年约三十七、八岁。(注:潘从理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师从梁漱溟,属乡村建设学派。在古蔺有名气,县志为之立有人物传。他在叙永联中与父亲同学,私交甚厚。他们创办的小学取名勉仁,也是因应梁漱溟的弟子在重庆北碚金刚坡开办了勉仁中学之故。)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他曾编辑两册国文,并用皮纸抄写表背装订成册,作为我们兄弟教材。那小楷写得和印刷的一样的精美。几万字的课文,无一错落。我长大后,一些年长的亲友在谈到父亲的情况时说,他的文章写得好,还背诵父亲写的精彩句段给我听。这都是我不知道的。我记得父亲的案头,常放置的成套书籍,有王阳明的《传习录》顾炎武的《日知录》......还订阅有《东方杂志》。在那个年代,在那个连报纸都很难见到的地方,订阅《东方杂志》的人是很少的了。这说明他既热衷旧学,但不守旧,也关注新的东西。如他多活些年月,也可能在教育方面多有些贡献。
父亲对我的教育,一直重视。他在泸州给我买了二、三十册少年儿童读物,都是人物介绍类的,如纪晓岚、岳飞、墨子、牛顿···等等。他在扉页上写了这样几句:“买书虽不易,但愿汝能读;口读书中文,志在书中人。”他给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说岳传。从发蒙开始,我读书就跟随他走。他开私塾馆,我就读私塾;他到南城小学教书,我就随他去读南城小学;他到川南师范工作,我就随他去读川南师范附小;他开办勉仁小学,我降一级也去读勉仁小学。
父亲的私塾馆第一次开设在家里,学生大约十来人,都是附近亲友子弟。我就在这里发蒙。我读的发蒙课本,既不是《人之初》也不是《百家姓》,而是《声律启蒙》,即“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的那种。然后从《大学》开始读完《四书》,之后读到《左传》。其间,加读唐诗。每日的功课:一、习字;二、阅读新授课文,和复习旧课文。所有课文,都要求背诵。每日每个学生都要到老师桌前背书,既要背新课文,也要背旧课文。学生们背诵的书,有多达四、五本、六、七本的。垒叠一大摞。那时的教学方法,就是重背诵,而不重视讲解让学生读懂。祖、父辈都是那样学习的。我的祖父那时已年近六十,但仍然熟记幼年读过的《四书》。我和大哥在室内夜读,他在室外乘凉,听到我们读错了的,便立即大声纠正,严禁我们读望天书。这就是那时的传统。在我读到《左传》一半的时候,父亲的私塾停办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以及开办了多长时间,我都记不清了。
父亲在花厅头开办的私塾,是专门教他家儿子的。学生仅有八、九人。我和大哥都去了,我是最小的一个,大约七、八岁吧!他们都坐成人桌凳,我则坐小桌小凳。他们读《左传》、《史记》、《昭明文选》,我则选读《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上的文章。先读一些“陋室铭”、“春夜宴桃李园序”等短文,而后选读唐宋八大家名篇。在这里我开始学习作文。读那一类文章,父亲则出那一类的题目,让我模仿着写。当然用文言文写。年纪小,书读得不多,肚里没有货,仅能作形式上的模仿。记得在读了三苏的“范增论”、“留族论”···之后,也写了论文,竟还得父亲的红笔圈点。但在他教我读了“进学解”和东方朔的“答客难”之后,我就写不出同样形式的文章了。父亲给我授课时,仅我一人,讲解简略,给大哥他们授课,讲解则详尽得多。我常在旁偷听。似懂非懂地留下一些概念性东西。如他讲的宋明重理学,清重考据,桐城派渊源等等。一次他讲《归去来辞》说,“心为形役”是古时候知识分子的心结,我觉得新奇,就留下了记忆。多年后,当我读到苏东坡的“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及张翰说“人贵得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随即弃官而去的故事,联想起来,确如其所说。
这个私塾馆,也开办得不长就停办了。停办的原因,没有留下记忆。这两次的私塾教育,对我这一生起着重大影响。主要是养成了传统的正统观念,养成了对国学的偏好。一些传统的思想,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体化的思想;讲求气节、人格、;讲求诚信,追求正义的思想,像自然应有的一样埋置在心里。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一种性格,一种价值判断。
03
过 年
从旧历冬月开始,家里就有了过年的气息。伯母、三婶、母亲几妯娌就开始忙着备办年货。厅堂空房里就陆续摆放晾晒阴米、汤圆面、猪儿粑面、黄粑面···的大斗筐。这些糯米面粉全是用碓磕、用细箩筛出的,很费时费力。汤圆面等本可以用磨浆沉淀的办法,可省时省力。但家里的人认为那样做不好吃、且不能长久保存,始终坚持这样做。更为费劲的是做玉兰酥,要把糯米粉蒸熟,再切成条晾干。为这些所以在冬月就开始忙起来了。这时,为全家缝制冬衣的裁缝也在家里摆起摊子,一做就是几十天。这个裁缝是远房亲属,善讲故事,我常听他讲聊斋三国。
接下来,就是杀年猪,腌制腊肉香肠。猪是自家饲养的。从选购仔猪、饲养到宰杀都由祖父决定。年猪都饲养两年,都有两百斤以上。它的油肉要供家里吃大半年,杀年猪必定在冬至。家里备有杀猪的石凳和灶,来帮忙杀猪的屠夫姓何,是老熟人。杀猪那天,家里很热闹,全家人动员,还要请人帮忙,先后要忙几天。因为猪杀了还要分割,还要装香肠···那天中午一定要煮一大锅萝卜猪杂汤,有一大盆回锅肉。我们喜欢的是炸酥肉,除大人给的外,还要偷着吃。熏腊肉和香肠是祖父的专业。他在室内搭一木架,上铺放腊肉,下面燃放树疙兜作火种,放上柏枝烟熏,每天他要守住熏几个小时,一直要熏半个月以上,而后收藏。我也去陪坐守望过。这样熏出的腊肉到了七、八月都不腐烂,照样很香,炖豌豆很好吃。
腊月下旬忙的是“汗黄粑”(即蒸黄粑)和“按麻糖”(即制作米花糖等食品)。黄粑一般用糯米粒做,但祖父说家传用糯米粉,不许用米粒。“汗黄粑”那天上午就开始磨豆浆,然后加入红糖、米粉,再用黄粑叶包成长方形。我们的黄粑都做得大,重约一斤多一个。蒸它要用大灶、大甑。甑内舖一些稻草,再放上黄粑,要烧煤火,蒸一晚上,到第二天中午才出甑。这可能是把蒸叫“汗”的意思。“按麻糖”则更麻烦了。要先熬饴糖,将糯米浸泡,再煮烂,加入麦芽,滤去渣滓,而后煮熬浓缩。同时,要将已阴干的阴米、玉兰酥条等用沙炒泡。这些准备好了,再由三叔糖果店里的师傅来家里制作。制作时间都在晚上。我们则守着等候吃糖。我记得有一次,家里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连锅都洗净放在灶上,等到半夜三叔才同技师扛一袋白糖回来,作完已经是黎明时光了。
过年敬神和照彩灯用的红蜡烛,也是自家制作。我们叫蘸红蜡棒儿。蜡烛用的棬子油,也是自备。早在七、八月就砍下结子的棬子桠枝暴晒取子,用棬子去换榨制的成品油。烛心也由祖母、伯母搓制。我见过祖父和父亲蘸蜡烛。他们用沙吊子,盛上热水,加上了蜡和洋红熬热的棬子油倒入吊子,将插在烛台上的烛心,倒插入砂锅,反复蘸油,即成蜡烛。
再有一项“打扬尘”活动,大约是在腊月二十三进行。就是大扫除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新年。
腊月三十正式过年了。这天家里要请人来帮忙办席,做九大碗。菜都是猪肉、鸡肉做的,如粉蒸肉、夹沙肉、烧白···等等。这些菜都做得多,不仅供当天吃的,还要准备节日中客人来吃的。年饭都安排在午餐,实际开饭都在下午三、四点钟,吃完已是黄昏了。我记得最热闹的一年坐满了两桌人。当天,还有一个重要事,就是频繁的祭神活动。这是我和大哥的事。
我们家里没有人信教,但设有神櫃,供有家神。神櫃设在堂屋,有两尺多高,有踏凳上下。供奉的就是一块黑漆木牌,上书“天地君亲师神位”,另有药王菩萨、财神菩萨、观音菩萨几座木雕像,有几个香炉和一个磬。祖父要求我们每日早晚都要烧香敬菩萨;敲磬要早三下,晚四下,寓意创业难,守成不易。但我们都没有坚持。而三十这天就得照办了。早上起床,就烧香敬菩萨。中午,要祭祖,供奉猪头全鸡,又烧香敬一次。晚上则次数更多了。有一年祖父带着我守岁,忙了一晚上,约五、六次祭神。现在尚能记得名称的有三次。一次是入夜时的接灶。灶神菩萨是腊月二十三送走的,现在要接回来。送时的供果要有饴糖熬制的糖块。这种糖很粘口,说把他的口粘住,免得他在玉皇大帝面前乱讲,打小报告。今天接回来,就用一般供果。其次,在深夜十二点封印,把家用的量具升、斗、称及印章用红纸封起来,放在供桌上,明年择吉开张才能启用。这时要烧香敬财神。最后一次在天将亮时“接天方”。在堂前坝子的四角点上香烛叩拜。意义是什么,我记不清了。可能是接四方诸神吧!
初一,人们都睡懒觉,起床晚,早上吃汤圆。初一至初三不能出门,初四后出门也要看黄历择吉日。但在这几日会有讨钱的人上门。我见过的有送财神的。来的人装扮成财神样。有打连枪、唱柳连柳的。即在一公尺多长的竹竿上,穿上铜钱,舞动撞击身上各部位,发出响声,伴唱柳连柳调。有喊叫拜年拜年,手捧一封白糖纸包来拜年的。一次,我真把他当作来拜年的,把纸包收了进来,母亲叫我快还回去。然后轻声说,那是做样子的,里面没有糖,他还要拿去走下家呢!这些人都得给钱,才能打发走。他们穿着都不像常年要饭的乞丐。
家里的长辈没有给我们发过压岁钱。只有到二祖祖家去拜年,她给过几个铜元的压岁钱。大人带着去亲友家拜年,曾得过一个毫子。毫子是银的,如小铜钱大,可换十个铜元。那时通行的是银锭、银元、毫子、铜元几种货币。我没用毫子去买过东西。
节日期间,最热闹的是耍龙灯。从正月初九夜开始,直到十五晚上,每晚都要耍龙灯。我们差不多每晚都要去看。几条龙从下街出发,穿城而过,一直耍到上街。在宽阔的地段则有人在四角架设风箱火炉,熔化铁水,用木板拍打铁水散出火花,泼向龙灯。叫烧龙灯。耍龙的人,都要饮酒御寒裸露上身,这样铁花直接滚身而下,才不被烫伤。同时,还要放鞭炮,有些恶作剧的人,把炮竹放在耍龙人的足下爆炸,耍龙的人要跳跃躲避,嬉闹取乐。龙灯过后有“抬龙”的,即上下街的人相互投掷火弹和炮竹。火弹用火药加硫磺硝石,用米汤调和晒干制成。落在人身上就会巴着燃烧。参与者不仅有青年,一些三、四十岁的成年人亦参与。大哥亦常自制火弹去投掷。我从未参与过。
在城郊有些大户人家,也烧龙灯。在院坝四角架起风箱烧铁水,拍火花、放鞭炮。主人要给耍龙灯的人发红包,请吃宵夜。有的人家还放烟火架。我在很小时见过。那是一个一米多直径大的折叠起来的圆形灯笼,吊在一根竹竿上。燃放时点燃底层引线即一层层的放下。每一层都有人物动作,表述一个故事。然后燃烧掉,引出下一层。领我观看的人曾为我讲述这些故事。我人小不懂得,只看懂孙猴子,扛着金箍棒,还撒尿。撒尿是用花炮喷出的火花表示的。制作技艺精湛。这应出自当时古蔺有名的装银匠杨小候之手。但我查古蔺县志杨小候传及有关章节都无烟火架的记载,这是八九十年代修誌之人根本不知道有烟火架之故。因为制作烟火架的技艺,在杨死后就失传了。见过或知道有烟火架的人很少了。在四乡则演唱花灯。花灯是两人对唱,男的叫唐二,女的叫幺姑(男人扮的)。一个演幺姑的告诉我,他们演出时,看的人多,热闹极了。春节的最后节目是偷青。在十五这晚去偷摘别人种的菜,主人不干涉。我曾邀约几个人去偷豌豆尖、蒜苗来下面和炒腊肉,走了几块地,都是主人早已采摘或被别人光顾过了的,没有什么收获。那夜天晴,月色如银,空旷四野,结伴夜游,还是兴趣盎然。
我青幼年时的家,是个大家庭。父辈没有分家,祖、父、孙三代共有十多人。祖父早年曾在县劝工局任公职,后师从名师学中医,并会堪舆,常为人看病,看地。但不以为业。他行医处方,常用附子,而且量大,人称火神菩萨。他除继承祖业分得六十担租谷土地外,还筹集资金主持修建了我家住宅。那是一个有二十余间房,有菜园、花园,约几百平方米面积的院子。我懂事时伯父已早逝,父亲是老二、教书,收入不丰;三叔开一糕点店也经营不善;靠地租收入仅可维持一家人生活。我过年留下的记忆,都是那个年代的。到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五、六年内父亲、祖父、三叔、伯母相继去世,家道更加衰落,就没有那些人和事了。
04
山里的亲戚
我们家里把父系亲属即同姓的叫家门;母系亲属即异姓的叫亲戚。古蔺姓许的很多,都住在县城里。那时人称许半街,意谓有半街的人都姓许。但同我们五代内的亲属不多,只有十来家,余均在五代以外。有姻亲关系的亲戚都在乡里,同在一个乡与我们相距几里路的有几家。另有几家则在山里。同这些山里的亲戚往来,虽然不多,倒留下许多记忆。
我的外祖父家在袁家沟,住在从古蔺到叙永大路边的山坡上。幼年随母亲回娘家时,外公还在,外婆已经死了,有一个舅舅。他们家算个收租吃饭的小地主吧!但并不富裕。母亲去了不知什么原因,还要做饭。我们去是夏天,常吃包谷汤圆。母亲要天麻麻亮就起床上坡去掰包谷、采摘南瓜尖和南瓜花。回来后脱粒磨浆做成汤圆,和南瓜尖南瓜花煮在一起,有甜味有清香,非常好吃。那不是现在所谓有机纯天然食品能赶上的。母亲一早上全手工操作做那么多事,现在回想起来,也令人惊奇!
舅舅常带我去山下大路边一小店玩耍。这个店卖一些火柴类日用品。有几个玻璃罐装一些糖果。舅舅买一个面上粘几粒芝麻、内包红糖的干壳饼给我,就算高兴的事了。在这个店里,我曾遇到一个挖煤炭的农民,带我去看他挖煤的煤窑。所谓煤窑就是一人来高的一个山洞,只能容一人进出。他挖煤时头上插一个亮油壶,裸着上身拖一个竹筐进去,挖满一竹筐,就拖出来。他说煤洞不深,再深了灯就不亮了。这里煤的质量很好,无烟,无异味,他们都用于冬季取暖,日常生活仍然烧柴。我在叙永读高中时,来去曾去舅舅住宿过。后来舅舅接了舅娘,两人都染毒吸食鸦片,以致家败人亡。听说外祖父早年,家道还好,母亲出嫁,曾给一条黄牛陪嫁。我家用不上,母亲就给山里人代养,母牛产子时分成。我十多岁时,还曾听他们谈养牛的事。
我们有个大姑婆嫁在长坝子周家,早寡,有二女。暑天祖父常去那里避暑。有一年祖父又去了,我同大哥在暑假中,也去那里耍。从我们家里去要走七十多里路。我们一早出发,先走三十里大路,然后在一个叫老山的地方爬山走小路。那时的大路上,常在小溪小桥的旁边有株大黄角树,树下则有人摆摊卖醪糟凉水。买一碗醪糟冲凉水喝,很解渴。但山路上没有醪糟水,我们渴极了,在一个山岚垭路边,找到一个沙氹,水很清亮,就捧起喝,清凉有甜味。到大姑婆家已是下午四、五点了,祖父削梨给我们吃,那是青皮梨,个大细嫩,水多很甜。祖父说周某家种的,才送来。
在大姑婆家,一些伙伴带我去扒地瓜吃。这是一种地上藤蔓植物结的果子,有枇杷大小,很甜,多长在石坎上或坟坝上。我们家宅边河坎上也有,但少去扒来吃。我们还相约去打马蜂窝,蜂窝吊在一株大树上,我们用石块去打遭到蜂群的追击,我按照同伴的呼唤,躺在地上,还是被马蜂蛰了两下,都锥在头上。回来后头痛欲裂,他们帮助取出刺抹上蜂糖,睡了两天才好。
大姑婆有两个周家侄儿,叫周锐、周钧(两人均是地下党员),已分家,但仍住在一栋房内。一天,周均说有条河有大塘,可弄鱼,相距十来里,约我们去耍。我们去了。临近时,要下一个高坡。坡上没有林木遮挡,仅有一些枯萎的包谷杆。从上往下看,陡势很吓人,我很害怕。大哥他们直着腰就走下去了,我却走得胆战心惊,有些地方,我只能抓住路边的包谷杆或灌木草草,侧着、梭着下。下到坡底,才算平静下来。下面实际是一大山沟,河床中堆垒着巨石。河已断流,只有些小水氹。周均说,大水塘还在下面,还要走一段路。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看的就回来了。回来后,我又发烧病了。他们说是吓出来的。又睡了两天。在大姑婆家耍了十多天,我们才回来。
我们还有家亲戚在令牌山,姓王,是三婶的后家(即娘家),但三婶姓范是古宋人,怎么令牌山的王家,竟成了她的娘家呢?原来三叔曾下聘王家女儿,已戴花(订婚),未过门(结婚)就死了。三叔与三婶结婚后,王家把三婶当作他女儿的“继足”,认作他们的女儿,三叔仍作他们的女婿,所以三婶就有了这个姓王的娘家。三叔在时,常谈他在王家当女婿,同他的舅母子(舅子的老婆)开玩笑的故事。他这个舅母子,患眼疾几近失明,有些抠。她做了一罈渣(读去声)海椒鸡,不放在公共取食的地方,却放在她卧室的床头下。这渣海椒鸡是将新杀的鸡,切成小块,和上生海椒米粉调料,放在泡菜罐内密封发酵保存。食用时取出蒸熟即可。三叔有意去偷取作弄她。去时,她正坐在床沿上,听到响动,发声追问,三叔利用她视觉朦胧的状况,装作她的丈夫,竟蒙混过去了。
令牌山距离我们家有七十多里,但王家每年都要派人来看望他们的二嬢即三婶。来的人背个背篼,装着冷窖粑挂面鸡蛋之类的东西。有几次还送打猎得来的野山羊腿。冷窖粑和山羊腿都是我们爱吃的东西。冷窖粑是用糯米磨浆发酵做成,晶莹透白,很甜。听说,这粑粑只能在高山地区冬天做,发酵时间长,不好掌握,弄不好就酸了。我们家做不成。有时长坝子大姑婆也送来,我们都把它当做珍品。野山羊肉很香,运气好,碰着伯母还在切弄的时候,我们在菜板上就拈着生吃很香。三婶有个舅子也常来,我爱听他讲打猎的事,讲他们打野猪、打山羊,还常打一种叫酸草狗的野物,说只能在室外炖,油多,很香。寄住在我家防空站的一个报务员,也听得入神,他与我相约在一个暑假去那里打猎。我们去了,结果正值农忙,人员邀约不齐,没有打成。
王家这门亲戚完全是旧时习俗虚拟出来的,而双方竟能确有其事地来往,绵延多年。期间,因为王家有女嫁到大村李家,三婶还由此又有了大村李家一门姨妈亲,这就是所谓竹根亲了。李家有个儿子名李鉦常来我家,叫三婶二嬢,并与我成了好友。他是地下党员,建国后,在古蔺做区长,后调隆昌中学任校长。
古蔺诗人许息卿(1913-1991)是我远房大叔。早年与我父亲友善。我高中毕业后也与他往来。他在勉仁小学教书时,我在勉仁小学寄住,与他同住一室。他吸鸦片,夜晚过足瘾后,需进食。他带了一个“五更饥”的灯作烹食用,但效果不佳。我则在学校食堂叫醒了炊事员为他煮面条。他常在床吟哼创作诗句,有时我也跟着作一两句,请他评判。1948年我在重大读预备班,中文系教授邵祖平亦写诗。中文系学生何中林要我向许息卿索取几首诗,他拿去给邵,看邵如何评价。我照着办了。后来许邵之间即多有唱和。
他的祖父辈在外做过官,是官宦世家。家道殷实。他家临街大门,比周边的门高,上绘门神几如人大。古蔺下桥可能是他家出资或领头修建。我记得40年代建桥一甲子,他家还为之举办六十大寿庆祝。他没有进过什么学堂,全是自学成才。解放后,他以教书为业。他写的诗词有三千多首。早年我曾见过他抄缮成册的诗集,即垒高近尺。可惜大部毁于文化大革命。现仅存八十余首,我抄得以下两首。
漫兴
水蓝波明雨渐残,蝉声正在碧梧端。
半床书聚右令运,一室心藏天地宽。
眼暗不劳分黑白,舌存聊可辩咸酸。
却将生事烦邻里,每馈新蔬助瓦盘。
茅屋
茅屋欹倾长绿台,柴门正对小溪开。
低檐有隙蛛先据,室无存储鼠不来。
眼底未妨成寂寞,胸中何物更崔巍。
泉声树影闲相伴,尽把生平付酒杯。
”
他把衰老、穷困、孤寂的生活,写得那么清新、生动、淡定而充满情趣。如:眼暗不劳分黑白,舌存聊可辩咸酸;如 低檐有隙蛛先据,室无存储鼠不来;如半床书聚右令远,一室心藏天地宽......这正是他潇洒豁达的生性。
华锟
2017.3.23草拟提纲
2017.11月复笔
2018.9.15完稿
文字 | 许华锟
图片 | 图1转自网络,其他旧照片由作者女儿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