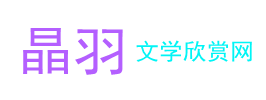驴子和他的买主读后感10字(驴子和它的买主读后感30字)
黑驴此时被拴在牲口市场的木桩上。
市场上的牲口大都比它健壮漂亮。它们的毛色都不错,不管是什么颜色的,都溜溜地贴在皮肤上,透出滋润的光泽,而黑驴的毛色却非常糟糕,虽然来时主人用扫帚梳理过,但积重难返,它还是显得很凌乱、粗糙、干涩,如一把乱草,大有一点就着的可能。不用说,这是一头可怜的驴子,一个命运多桀、邋遢的、不讨人喜欢的驴子。
黑驴静静地站在树桩前,它的主人不见有买主来过问,已经显得很不耐烦了。后来过来几个人围着它看,挑挑剔剔,主人虽然喊出了很低的价,但他们还是不屑地走掉了。
黑驴最终还是被人买走了。现在,这个人就牵着它走在回家的路上。这个人名叫李庆来,四旬的年纪,是李家屯的人,黑驴现在跟着他就是走向李家屯。眼下正是仲秋时节,太阳光不冷不热,田野里充满了绿色与和谐。黄土大道宽宽展展地延伸着,穿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李庆来这人衣着相当朴素,脚上还穿着老式自制的布鞋,头发比黑驴的皮毛好不了多少,黄而凌乱。后背微驼,背在屁股上握住缰绳的双手粗糙不堪,这是劳作与营养不良的缘故。黑驴会由此感到李庆来的家境并非比卖掉它的旧主人富裕多少。
黑驴跟着李庆来回到了李庆来李家屯的家。李庆来并不急于跨进院门,而是朝院里喊叫了两声,立即走出一个女人,这便是李庆来的妻子。观眉色,这女人要比李庆来小一些,虽不漂亮,但白白净净,匀匀称称,身段丰腴有余,又因眉心有颗显亮的黑痣,反倒显出几分迷人与娇艳。女人高兴地跑出来,以为李庆来买来一头什么像样的驴,这一看,脸色就沉了下来。女人说:“怎么买了这么个破驴?”李庆来讪讪地笑:“你不懂,这驴没喂好,喂好了一上膘,就会有神气。就像你们女人,喂不好干柴似的,让人看了没有一点饥渴感……”女人脸盘忽地蒙上一层红晕,骂了李庆来一句,这才拿出一节红绳套在黑驴脖子上,让黑驴走进了这个家庭。这节红绳预示着黑驴能给他们带来如意和吉祥。
黑驴两只黑亮的大眼睛顾盼着眼前的这个院落,与黄河中下游流域所有的民房建造一样,五间大瓦房,坐北朝南。院子很大,光秃秃的,墙角堆放着一些柴草及乱七八糟的东西,黑驴的草棚就搭在南墙根门房边。棚口有一口三尺长的石槽,石槽里已拌好了草料。黑驴站在石槽前,埋头进去,一边吃草料,一边看着北屋檐下的李庆来和他的女人,听着他们的谈话。
几天后,黑驴就看出了这个家庭的一些内幕。这一家只有三口人,李庆来的女人并不会生育,收养的别人的儿子眼下正在镇上念初中。李庆来很怕老婆,家里的一切都是女人说了算。而且很快黑驴就发现了一个秘密,李庆来的女人与村长有奸情。
那天下午村长来了。村长装作顺便看看的样子,头在院门口向里探着,先看见了黑驴这才看着李庆来走了进来。村长说:“听说你家买了一头好驴,看看是什么好驴。”村长将近五十的年纪,身体矮矮胖胖的,满脸慈祥的微笑。李庆来见是村长,忙递上烟。村长踅到黑驴身边,用手掏开驴嘴摸摸牙,拽了拽黑驴干瘪的皮肉,叹息说太瘦了,能像你嫂子那样胖就是好驴。嫂子就是村长的婆娘,李庆来嘿嘿地笑着不说话。村长瞟了李庆来的女人一眼,女人正在屋檐下做活,低眉垂眼并不吭声。村长说:“庆来,有件事你干不干,村部卸一车水泥,晚上看一夜三十元。”李庆来还未答话,屋檐下的女人马上说:“看,一夜三十元还能不挣?”一句话定了。村长松口气说:“那你晚上按时去村部,丢了水泥可要赔的。”村长说这话时一脸的严肃。
这个时候,黑驴并没有看出其中的阴谋,它怎么会看出村长是在搞阴谋呢?看着村长慈祥的面容和关怀别人亲切的口气,以及对工作负责的态度,黑驴想这样的村长不愧是个好村长,村长都像这样,农民不就大有希望了?谁知到了晚上,黑驴却发现自己的这种想法完全错了,村长与白天大不一样。当时夜刚降临,李庆来夹着被褥去了村部,一个黑影突然从院墙上翻了进来,“腾”地一声落地,吓了黑驴一跳。黑驴停止了吃草,机警地耸耸耳朵,吐吐地打了两个很响的喷嚏。黑影急忙溜到黑驴边,轻轻地抚摸黑驴的毛发,黑驴这才看清黑影竟是村长。
黑驴吃惊极了,怎么会是村长呢?白天和蔼可亲的村长怎么到了晚上会这么利索地翻别人的墙头呢?
村长轻车熟路地进了北房,顺手将门关了。黑驴正在为女主人的安危担心呢,屋里的说话声却清晰地传了出来。女人责备说:“谁让你翻墙的,不是说好八点整我去开门嘛。”村长说:“我等不及了,这些日子庆来老在家,找不着机会,憋得我好难受。”女人说:“这下有机会了?拉水泥干吗?”村长说:“那是给我家拉的水泥,先卸在村部让庆来看一夜,明天再找车转回去。”女人笑:“这么说,今晚的三十元钱也是你出的?”村长笑:“我出这冤枉钱干么?那还不是村里的,村里的还不是摊在你们身上的,我花你的钱,还要睡你的觉。”女人假装生气地说:“你这是公款嫖娼,是犯法的。”村长说:“三十块钱也算嫖娼?”女人说:“那我家的村组提留、建校款、维修款乱七八糟加起来也有一千多块,你都免了,这算不算钱呢?”村长说:“看把你越说越金贵了,几天不见,你就能得飞起来,看我怎么收拾你。”说着,屋里的灯就忽地灭了。
黑驴这才知道这是一个串通好的阴谋,主人李庆来蒙在鼓里了。
黑驴想,这样的村长也是村长?村长这样做太对不起我的主人李庆来,这女人也对不起我的主人李庆来。我的主人现在孤零零地睡在村部水泥堆旁,你们却在屋里寻欢作乐。黑驴想,李庆来把我从困苦中解救出来,让我过上了好生活,我要忠实于我的主人,我要阻挡你们。黑驴在草棚里焦急地踩着蹄子,围着石槽焦急地转悠。它摆脱不了缰绳的牵制,但它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声音,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于是黑驴就嗷儿嗷儿一阵紧似一阵叫起来。黑驴的叫声是那样的宏亮高亢,在夜深人静的晚上,一阵激越聒耳的驴叫声,三里五里也能感到震撼,何况它面对的是两丈开外的屋子,何况村里面还有不少它的同伴,它们听见了黑驴的呼叫怎能不遥相呼应呢?果然,黑驴的叫声刚刚落下,村里的驴子都此起彼伏地叫起来。屋里的灯忽地亮了,女人慌慌张张地披衣跑出来,用手电照着院门,照着驴圈的驴,以为来了夜贼,看了一遍,这才松了口气。村长穿着短裤披着衣服跑出来问:“没事吧?”女人说:“没事,我以为有贼了。”转回屋里刚关灯,黑驴又快活地叫起来。灯又亮了,女人与村长又跑出来。这一回,村长径直走到黑驴跟前,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黑驴,他怀疑黑驴是在故意捣蛋。村长问:“你家的秤砣子呢?”村长走到黑驴的身后,还没等到黑驴弄清是怎么回事,那秤砣子就紧紧地吊在它的尾巴上了。黑驴想,他们这是干什么呀,用这玩意能阻挡我的反抗么?谁知屋子里第三次关灯时,黑驴的尾巴竟然摆动不起来,黑驴就再也不能发出高昂的声音了。黑驴急坏了,绝望中产生了愤怒,愤怒的它只能用呜呜的低鸣抗议着。
黑驴的抗议还是起了作用。后半夜,村长离开李庆来的家时,气呼呼地说:“今晚没睡好,光分心,都怪这匹瘦驴。”说着拿了一根树条,在黑驴身上狠劲地抽了几下。
第二天早上,李庆来夹着铺盖回到家里,女人接过他的三十元钱,脸上平静得像一潭水,不见丝毫慌乱、不安或内疚,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李庆来竟也毫无觉察,连屋里的蛛丝马迹,连气味,连墙上的痕迹也留意不到。
在以后的几次偷欢中,黑驴再也不会让村长把秤砣吊到它的尾巴上,只要村长一靠近,它就急促地转动身子,跺蹶子。村长险些挨了重重一蹄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让女人用布料蒙住黑驴的眼睛,不让黑驴看见屋里的灯光,看不见灯光,看你黑驴怎么叫唤。但黑驴却惊觉地竖起了耳朵,聆听着屋里的响动,每当它听见屋里有那种惬意的忘乎所以的声音发出时,黑驴就不失时机地叫起来。再后来,村长连欢快的声音也不敢发出了,他在忍气吞声地干着那事。再再后来,村长实在按捺不住了,就恼火地说:“不干了,晚上再也不干了,这头该死的驴子搅得我心神不安,以后我白天来。”女人说:“白天他在家,可不方便。”村长说:“快种麦了,这茬地要犁了,等他出去犁地时我就来。”
果然没几天,村里的人就开始犁麦闲地了,李庆来也加紧给黑驴喂料,拾掇犁地的工具。这天上午,村长来到李庆来家问犁地的事,要庆来快点动手,犁完了好给自己那几亩地犁犁。李庆来说要么就给你家先犁吧,我家晚点也没啥。村长说不行,还是你家先犁,我家晚点没啥。李庆来说那我今天下午就开始犁了。村长说:“快点犁吧,等不及了,要种麦呢。”
虽然已到了九月下旬,但午后的阳光依然带有几分毒气,烤在人们的身上热烘烘的难受。村长在喇叭上喊话了,歇晌的农民都在不同的地方侧耳细听。村长这一次没有督促今年的特产税与村组提留,而专门讲了村风。村长说咱们的村风很不好,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有的人还呆在家里无动于衷,麦地早犁几天怕什么,怕明年麦子长得好了是不是,我都等不及了,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再说这早种晚种,明年的收成是不一样的,我要求大伙从今天开始必须投入耕地秋播的高潮中去,谁呆在家里或在村里乱转悠,我就取消谁家的“文明户”评选资格……
李庆来拉着架子车,黑驴拴在车后面向地里进发了。它与主人走了好长时间才走到地里。李庆来卸下化肥袋开始撒化肥,黑驴就站在地头,看着李庆来稀疏的头发、微驼的后背与粗糙黧黑的皮肤。明年这一块地要打出几千斤的麦子,这都是李庆来的血汗所得,却养白了家里的女人。村长这时肯定已到了那女人的身边,而李庆来却在这里撒化肥。黑驴很急地打着喷嚏,嘿哇嘿哇儿地叫起来,李庆来却全然不知,依然撒他的化肥。后来他卸下铁犁,解开缰绳,准备将黑驴套上去,不料黑驴却挣脱开向前跑出几丈远。李庆来吃惊地望着黑驴,他不相信黑驴会这么不听他的话。他伸着手,嘴里说着好听的话向黑驴靠近。黑驴当然不会上当,而是折身跑出了田地,跑到路上。李庆来追了上去,黑驴撒开蹄子急跑,李庆来不得不向回追。黑驴跑一段停下来,啃几口路边的野草,等李庆来追近了它再跑,这样三跑两站就进了村子。
李庆来的院门果然紧闭,黑驴在门前放开喉咙叫起来,久久不息,直到满头大汗的李庆来追到门前抓住它的缰绳。李庆来看见了紧闭的院门,眉头皱了皱,上前拍了几下,喊着儿子的名字。延误了几分钟,女人这才开了门。这一次她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惊慌,但行动却一丝不乱。女人说:“我睡了一会儿,怕生人瞎闯进去。你咋回来了?”李庆来说:“驴子挣脱了跑了回来,我以为家里出事了。”女人说:“好好的能出什么事。快去犁地吧。”李庆来就牵着黑驴往回走。这个时候黑驴猛然发现村长在后面的一条街上一跛一跛地走着,不用说那是刚从李庆来家后墙上翻出时跌的。
有了这一次,村长肯定更加恨黑驴了。几天以后,他就得到报复的机会。
那天早上,李庆来牵着黑驴去给村长家犁地,村长领着他们来到了自家的地头。村长说:“就这块地,犁吧。”李庆来和黑驴就干了起来。黑驴拽着犁,一口气跑了十多个来回,累得气喘吁吁,全身淌了汗水。黑驴吃力地走着,有时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李庆来说:“歇会儿吧。”村长不满地说:“这个懒家伙,一走一停的,用鞭子打。”李庆来说:“这些日子,它独自一个已犁了十几亩地了,驴岁数还小,又没喂好,我看还是歇会儿吧。”村长说:“你就知道心疼牲口,畜牲有什么好心疼的,我干了一辈子农业,还不知道怎样对付畜牲?”说着就拿起鞭子向黑驴猛抽,“啪啪”,一下又一下,每一下都打得黑驴眉头一皱一皱的。黑驴拼命向前挣着,鞭子还是不断地落在它的背上和腿上。后来村长索性用鞭杆抽打黑驴,黑驴一惊一乍地向前猛蹿。李庆来乞求般地说:“好了村长,少打几下吧,它已经犁了。”村长跛着脚,一颠颠地跑着喊:“这是犁不动?谁说犁不动,这不是跑起来了吗?这个奸诈的家伙,真是欠揍!”这样抽打了一会儿,黑驴真的是走不动了,它索性卧倒在地上,任凭村长的鞭杆啪啪地落下来,死也不走了。
村长扔了鞭子,骂着黑驴的祖宗回去了。黑驴卧在地上,急促地喘息着,全身的疼痛已全然感觉不到。李庆来走近黑驴,用那粗糙的手掌不住地抚摸着它身上的每一道鞭痕,双手颤抖着,心里在骂着村长的狠毒。一会儿,村长牵着匹红马回来了,让红马做黑驴的帮手,这样一来,黑驴虽然还感到吃力些,但到底轻松了许多。新来的红马与黑驴共同拽着一张犁。红马说:“兄弟,你受苦了。你这般瘦弱,还要独自一个犁这么多的地,却落得这般待遇。”黑驴说:“我命苦。”红马说:“兄弟你还信命?你不要丧气,我不是来了吗?有我帮着你,你不会受苦的。”红马用她的身体不住地抚摸黑驴的身体,黑驴顿时感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黑驴这才看清身边的这匹红马是一匹非常年轻漂亮的异性,黑驴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这样年轻漂亮的母马,别说年轻漂亮,就连一匹丑陋衰老的母马,有生以来它也没遇到过。它总是孤独地居住,被人类时刻管制着,哪有一星半点的机会接近异性呢?黑驴想,这不是做梦吧?
黑驴与红马在埋头劳作中窃窃私语,它俩鼻息相通,彼此闻到对方身上迷人的气息。它们相互诉说着各自苦衷,相互倾诉着各自的爱慕与恋情。血液像炭火般烧起来,它们都感到了对方的炽烈,这不是爱的呼唤又是什么?它俩都意识到了,属于它们的时间只有今天下午这几个时辰了,村长的二亩地一犁完,也就是它们相会的彻底终结。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若不再去追求自己的爱,岂不是枉活一生?红马在期待着黑驴,黑驴终于奋不顾身地跳了起来,与红马相拥一起,只是由于绳索的羁绊,使它们不能如愿以偿。村长惊叫起来,大骂“流氓”,用粗粗的树棍拼命抽打黑驴,黑驴躲着村长的树棍,拽着红马在地里转来转去地躲逃,不一会儿,黑驴和红马都挣脱了套绳,齐头并肩跑到了远处。
红马和黑驴的爱情真的成功了,当着村长的面,温柔的红马和年轻的黑驴迸射着爱的火花。黑驴用它强劲有力的臂膀去拥抱红马,用它炽热无比的激情去融化红马。这个时间,站在远处的村长脸色苍白,嘴唇哆嗦,目光变得阴鸷不堪。村长喘息着,喃喃地骂:“流氓,流氓,真是流氓……”声音越来越小。
十月上旬,乡下进入了紧张的麦播期,黑驴和李庆来更忙了。这一日,李庆来牵着黑驴从地里种麦回来,看见村长站在村口大路边与人说话,出于礼貌,他对村长说:“你家的麦子种了吗?要不用我家的黑驴种吧。”村长说:“不用了,不用了,你家这驴子太不是东西,好吃懒做,还是个大流氓。”旁边的人吃吃地笑。李庆来也笑着说:“村长不是在糟贱我的驴子么。我看我的驴子挺不错的。”村长撇着嘴说:“你这驴子还不错?白给人也不要。要膘没膘,要肉没肉,干起活来耍滑头,见了母马就不走,流氓到家了。”旁边的人看着黑驴哈哈地笑出声。黑驴窘极了,村长尖刻不堪入耳的语言充满了它的脑海,让它感到了耻辱和愤怒。当它跟着主人经过村长身边时,村长还在大肆地侮辱它,而且这时竟然扬起手来,就要一巴掌拍在它的屁股上了。黑驴已无暇思考,本能地跃起后蹄,狠狠地甩了一蹶子。这一下正中村长裆部,村长一下捂住那地方蹲在地上,半天发不出声音来,随即又滚在了地上,吭吭哧哧的,脸色苍白如纸,汗如雨下。李庆来与村人大惊失色,慌忙扶着村长去了医院。
村长住院后,李庆来与女人都去伺候村长了,三天时间都没回家。黑驴被拴在窝棚下,饥肠辘辘。石槽里一根草也没有了,黑驴吃不到任何东西,只好死啃木桩上的缰绳结。黑驴用钝齿去咬它,用柔软的嘴唇去磨蚀它。黑驴的嘴唇早就磨烂了。黑驴终于在第二天黄昏弄断了束缚它的缰绳,跑到院子一角的草料袋前,尽情地填充它的空腹饥肠。吃饱喝足后,它享受着有生以来最大的自由,在空荡荡的院子里跑跑停停转转蹦蹦,村长这时在干什么,它完全顾不着了。
第三天傍晚,李庆来独自一人回来了。他看见被黑驴弄得满目狼藉的院落与正在院中逍遥自在的黑驴,肝火上来了。他把黑驴拴住,迅速拎住那杆驴鞭劈头盖脑打向黑驴。他的面孔由健康的赤黑已变成了死灰。他的眼睛红肿,嘴唇烧起了一串白色的水泡,有的溃烂后流着一丝发黄的液体。他一鞭又一鞭地抽着黑驴,每打一鞭都要重喘一口气。黑驴在棚下本能地躲闪着,但鞭子还是重重地落在它的身上,后来它实在没处躲了,只好缩在一角,惊恐地看着愤怒的主人。最后它只有瑟瑟地卧在了地上,悲哀地呻吟着,眼中淌着泪水。
李庆来终于扔了鞭子,抱住黑驴的头呜呜地哭起来。
李庆来呜咽着对黑驴说:“好伙计,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我不傻,我早就知道村长睡我的女人,但我没有一点办法。他是村长,有权有势,我真的得罪不起他。我不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我是一个没本事没出息的男人,我这种男人只有这样无奈地活着。”
李庆来说:“其实我真希望你一脚踢死他,大家都希望他这一次就一命呜呼,但是他没死,他没死灾难就会降临到我的头上,他出院后就要我包赔他的损失,我怎么赔得起呢?”
李庆来说:“村人的日子都不怎么富裕,但这一次都得花钱去医院看望他。起初去的人并不多,后来听说他的女人拿着本本记录人名与礼品,于是全村的人几乎都去了,都带了很多东西,仅鸡蛋就收了一千多斤,卖鸡蛋的小贩子不断地从他的病房里向外搬鸡蛋。水果滋补品不计其数啊!”
李庆来说:“村人这一次担心哪,大家都希望人家好快一点,既然死不了,就光光堂堂出院吧,不要留什么后遗症,要么他会以公伤为由向村民们摊派费用了……”
十天后,村长出院来找李庆来。村长平平静静,脸上依然带着笑容,李庆来却脸色发白,心已提到喉咙眼了。村长说:“这一次伤得不轻,真是伤到要命的地方了。不瞒你说,我那东西真的有点不大方便了,这是我一辈子的事,虽是驴干的,但它是你的驴,你是它的监护人,闹到法庭,不让你赔十万八万,也得赔三万五万……”李庆来的脸色更白了,浑身不由得哆嗦。村长说:“不过话说回来,念我与你女人一片深情,这笔款子我就不想追究了,但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今后我来你家,你不但要尽快躲开,还要替我在外看着点;第二,你的黑驴得归我,我得拿它出口气……”李庆来怔怔地看着村长不知所措。村长沉下脸说:“答应不?不答应我走了。”说着转过了身子。李庆来慌忙拉住了村长,木木地瘫坐在地上。
村长说:“这就好了。”出了屋走到院子里,村长的两个弟弟也来了。村长拦住他们说:“别动,让我来。”便拎着一根木棒,杀气腾腾地走向黑驴。黑驴警觉地昂起头,扯紧缰绳向后退着,脚下急速踩动。村长走到石槽前,看准黑驴的头部就给了一下。黑驴一躲,打在了它的左膀子上,让它感到钻心的痛。黑驴向前一跃,前蹄踏上石槽,村长说:“我叫你能!”一棒又劈住了黑驴的脖子。黑驴仓惶溃退下来,呜呜地叫着,四蹄奋力刨脚下的粪土,棚下一片粪屑迷蒙。村长侧身又是一棒打住黑驴的腮帮,黑驴立刻感到眼前支离破碎,红色泡沫飞扬。第四棒打来时,黑驴奋力一跃,崩断了缰绳,飞出圈棚,跌落在地上。村长刚要上前袭击,黑驴已猛然跳起,后蹄击住了村长的胳膊。村长大叫一声,扔了木棒逃到院门外去了。
村民被惊动了,纷纷聚到这里,院墙上密密麻麻爬满了大人或孩子。有人低声说:“这驴马上就要被村长打死了。”兴奋、好奇、惶惑、怜悯、不平、气愤等,都写在了村人的脸上。这时,院里村长的两个弟弟各执铁锹和粪钗开始包抄黑驴,黑驴一次又一次地冲出他们的夹击,它把希望寄托在南面的院墙上。它奋力向南墙扑去,趴在墙上的人“哗”地全退了下去,但它还是没能跃过墙头。
几分钟后,黑驴将村长的一个弟弟踢倒在地,另一个弟弟惊叫着拖着受伤的弟弟仓惶躲到院门外去。形势对黑驴非常有利,村人中有的忘情地为黑驴的勇敢鼓起掌来。不料掌声未绝,却见村长端着一杆猎枪走进了院子。
大惊失色的李庆来从北屋里跑出来,他说:“村长叔,村长叔,你万万不能伤害它。”村长只一脚就把李庆来踹开了,“嗵”地一枪打去,黑驴遍体是伤,鲜血直流。村长压上第二颗霰弹,受伤的黑驴意识到危险再次降临,突然在院子里狂奔起来。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两个来回后,黑驴正好奔至南墙前,只见它腾空一跃,飞出了院外。村人慌乱中为黑驴让出了一条路,黑驴一路滴血跑出村去。等到村长他们大呼小叫追到村外时,黑驴已倒在路边死去……
冬天到了,村子南边的斜坡上堆起了一个土堆,庆来把黑驴葬在了那里。闲着的时候,庆来总会望着黑驴的坟墓发呆。他的脾气突然变坏了,无端的发作与大打出手,使往日专横而不安分的妻子老实了许多。而且每次遇到村长时,他的眼光便充满了仇恨和愤怒。这种眼光火辣辣地逼向村长,总是把村长弄得心惊肉跳,惶惶夺路而逃。
更麻烦的事情让村长遇上了,不知什么原因,一到晚上,他总能听见黑驴在房后大叫,真真切切。他壮着胆提着猎枪追到房后,却什么也没有看见,有的时候大白天也能听到驴叫,等他警惕地站起来细听时,那叫声又立刻消失。后来村长又去偷偷地找过李庆来的女人,回来后往往都在半夜睡梦中被驴叫声惊醒,惊出一身冷汗。村长家里的人都被村长的神经质弄得胆战心惊的,请来了巫师为他作法,但却无济于事。村长的身体越来越弱,躺在床上缄默不语,他常常会惊恐地对家人说:“听,又是它在叫,它又来了……”